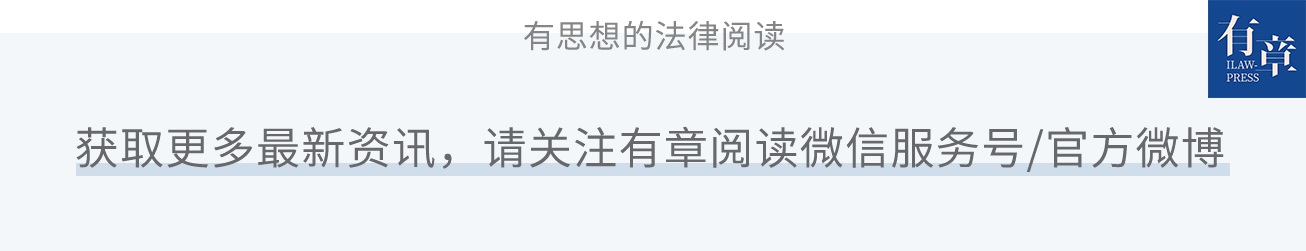法律出版社编辑整理
如果不出所料,下月关于中菲“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一经公布,“海牙仲裁庭”将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定将产生不小影响,这一点似乎也成为一种必然。而依照目前的情况判断,“海牙仲裁庭”5位仲裁员中的4位,都是日籍人士负责指定的,而整个裁决方向由欧洲人主导。此刻的西方诸国亦正在等待仲裁结果出台,并意图对中方实行全面围剿。特别是随着而29日爆出的实体问题裁决公布日,所谓“仲裁庭”在海牙对本案将来个国际法上的定纷止争,并且作出了将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终决性的裁决,“海牙仲裁庭”逐步走入中国人视野,但“南海仲裁案”其神秘的面纱仍未完全揭开。而今天我们推送这篇内容以期能看进门道。
要弄明白“海牙仲裁庭”有点复杂、有点专业的身世,首先要了解“常设国际法院”的历史,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四种“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
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是根据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于1900年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它是当前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法院由从事行政性工作的常设行政理事会、国际事务局、以及一份由联合国秘书长保有的“仲裁员名单”构成。“仲裁员名单”由每个缔约国各自遴选的4名法学专家组成。常设仲裁法院为国家、国家实体、政府间组织、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服务。这个法院从清政府到现在,中国人一直都在里面存在。
常设仲裁法院于1900年根据首次海牙和会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成立,是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回顾历史,中国是最早参与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活动的国家之一。
早在清朝期间,当时的清政府先后派杨儒、陆宗祥等人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会,并于1904、1910年先后批准了1899、1907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是常设仲裁法院的原始缔约国。
废除帝制后,中华民国继承了条约和法院成员资格。1972年法院行政理事会通过决议终止台湾当局在法院的席位。
1993年11月22日,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恢复在法院的活动,并指派李浩培、邵天任、王铁崖、端木正为仲裁员。
2009年5月4日,时任外长杨洁篪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指派邵天任、许光建、薛捍勤、刘楠来为仲裁员。
相比于司法,仲裁赋予了当事方包括指派仲裁员、协商仲裁程序在内的更大自主性,对仲裁结果有更多的可预见性,因此,国际仲裁不仅比国际司法拥有更加悠久的历史,而且自常设仲裁法院成立以来至“二战”结束后,其审理的案件数量也比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CIJ)审理案件的数量多。然而,自从1946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Court of Justice, ICJ)成立以来,常设仲裁法院的案件数量却急剧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与联合国其他机关密切配合,代表了战后国际秩序,为国际社会全体成员所认可;另一方面,国际法院的组成、职能、程序等事项由《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规则》等组织文件所明确规范,管辖权范围较少存在争议。上述条件为国际法院的良好运行、发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引入强制仲裁,也意味着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参与构建国际海洋秩序。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利用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国际争端。为了更好发挥法院职能,一些国际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开始引入法院的仲裁机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就是其中之一。
《公约》规定了四种“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即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一个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间,有权以书面声明的方式自由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程序;如果缔约国没有选择任何一种强制程序,或者接受的并非同一种强制程序,则应被视为已接受《公约》附件七所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仲裁法庭行使职权便是由常设仲裁法院负责。
与此同时,《海洋法公约》下的强制仲裁,还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建立了关联。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公约》规定于1994年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职能是解决由于解释和适用《公约》条款而产生的争端和问题。法庭总部设在德国汉堡,全庭由21位法官组成,并设海底争端分庭以及若干特别分庭。仲裁法庭与海洋法法庭的关联就在于,如果仲裁庭不能经当事双方协商一致组建,那么仲裁庭的组建工作就落在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肩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利用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国际争端。为了更好发挥法院职能,一些国际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开始引入法院仲裁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其一。这种有益尝试的出发点不错,但效果却事与愿违。《公约》生效20多年,利用国际法院解决海洋法争端近20件,诉诸仲裁庭的只有10件。主要是,《公约》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异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争议和漏洞,而仲裁又作为“强制程序”可被争端一方单方面启动,给一些并非为善意解决争端的国家留下把争议复杂化的余地。仲裁庭也存在任意发挥“自由裁量权”、曲解国际法规范和当事方意图的现象。
然而,自“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组建时起,由四位欧洲人主导的法庭就让人怀疑其能否具有代表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特别是亚洲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它的裁决证明,仲裁庭的司法理念超越国际社会普遍现状,是偏激和不公正的。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CA)成立常设仲裁法庭,庭长是日本籍的柳井俊二(Shunji Yanai)。柳井俊二已任命波兰籍法官斯坦尼洛夫帕夫拉克为仲裁员,代表中国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仲裁员。柳井俊二又任命德国籍法官吕迪格.沃尔夫鲁姆为仲裁员,代表菲律宾在此案的仲裁员。
柳井俊二,日本人,1999年至2001年曾担任日本驻美大使,2005年起出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2011年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任期三年,2014年6月,再次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任期至2017年6月。他还担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的私人咨询机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2014年5月15日,曾向日本首相安倍提交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也正是此人。
以下是柳井俊二指定出任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五名仲裁员:
1. 波兰籍的斯坦尼洛夫.帕夫拉克(Stanislaw Pawlak),仲裁员 - 指定代表中国。
2. 德国籍的吕迪格.沃尔夫鲁姆(Rudiger Wolfrum),仲裁员- 指定代表菲律宾。
3. 加纳籍的托马斯.门萨(Thomas A. Mensah),主席仲裁员。
4. 法国籍的琼皮埃尔.柯(Jean-Pierre Cot),仲裁员。
5. 荷兰籍的阿尔弗莱德.松斯(Alfred H. A. Soons),仲裁员。
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法为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所创设,为国家间交往服务,而非相反。也正因如此,凡是不能正确认清自身角色和职能、试图凌驾于大国外交之上的国际机构,必定事与愿违。
不公正的司法和仲裁必然导致当事方拒绝接受裁决。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统计,从1946年至1965年间,国际法院所有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3%,其中强制管辖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0%,而在1966至1985年的二十年间,国际法院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在此期间,所有强制管辖案件均未得到执行。1986年至2004年,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仅为29%,除通过特别协议提交法院的案件,执行率仅为17%。
自1946年至2004年,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44%,强制管辖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33%。当事国完全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主要有:“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被告方阿尔巴尼亚;“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美国诉伊朗)被告方伊朗;“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国)被告方美国;“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被告方乌克兰。
此外,国家不完全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案例主要有: “陆地、岛屿和海洋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原告方萨尔瓦多;“领土争端案”(利比亚和乍得)中的利比亚;“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国)被告方美国;“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墨西哥诉美国) 被告方美国;“拉基玛洛大坝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中的当事双方;“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域划界争端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被告方尼日利亚。
难以执行的案件,往往都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以及其他重大利益关切,即使作出判决也并不能让当事方定纷止争。
按理说国际司法和仲裁等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良药,但失去约束必将导致副作用。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上,国际秩序是通过各个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加以实现的,特别是大国在各自国家利益的支配下、通过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实现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调整乃至剧变。
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介入国际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建构国际秩序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可控性进一步减弱。就南海争议而言,国际仲裁的介入使中国在地区海洋秩序问题上的话语权弱化。而逐渐强化并不断扩张的仲裁机构权力,则为周边国家所乐见。可以预料,仲裁庭作出的最终裁决,将可能否定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基础,以及国在断续线内的主权权利。在仲裁庭盲目扩张管辖权、无视沿岸国的合法合理主张的情况下,《公约》缔约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加剧,仲裁裁决的社会效果将越来越差。下面看看国内官方机构以及国际法律人士对于“南海仲裁案”即可窥见一二。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国际法。
第一,中菲通过一系列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早已就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协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仲裁程序不适用中菲南海有关争议。
第二,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不在《公约》的调整范围内,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第三,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第四,菲律宾无视中菲从未就其所提仲裁事项进行任何谈判的事实,偷换概念,虚构争端,未履行《公约》第283条就争端解决方式交换意见的义务。"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下称《裁决》),认定菲律宾所提全部诉求均构成中菲两国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裁定对菲律宾部分诉求拥有管辖权,并将其余诉求的管辖权问题保留至案件实体阶段一并审理。这是一项从认定事实到适用法律都充满错误的管辖权裁决。该裁决至少存在以下六大谬误:
第一,错误地认定菲律宾所提诉求构成中菲两国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第二,错误地对不属于《公约》调整而本质上属于陆地领土主权问题的事项确定管辖权;
第三,错误地对已被中国排除适用强制程序的有关海域划界的事项确定管辖权;
第四,错误地否定中菲两国存在通过谈判解决相关争端的协议;
第五,错误地认定菲律宾就所提仲裁事项的争端解决方式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
第六,背离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和宗旨,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中国国际法学会认为,仲裁庭对仲裁事项具有管辖权是仲裁程序赖以进行的前提,也是其最终裁决产生法律效力的基础。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出的所有仲裁事项均没有管辖权,其关于管辖权问题的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其下一步就实体问题所作裁决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中国当初没有参与仲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菲律宾滥用公约强制程序,单方面提起仲裁,实质是要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中国当然不会接受和参与。中国未出庭提出抗辩管辖权,不愿意因此被拖入实体问题的仲裁,这一点在仲裁庭初步裁决中也有表现。但不接受、不参与并不代表毫无作为,去年外交部也发表了关于管辖权的《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对于明显没有管辖权的仲裁庭,它有什么资格作出所谓的裁决,有关裁决充其量只是代表了那些仲裁员个人的观点,对于这样的裁决,中国也是绝不会承认和执行的。“
“海洋法是近年来国际法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目前对于海洋法的误解误读都很多,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某些同志对此理解较为片面,另一种原因则是别有用心。其中一种有待商榷的观点,就是退出公约。此种观点的逻辑问题在于,南海问题并不全部是用海洋法公约来解决的,最典型的就是岛礁领土问题。用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南海问题,这一说法首先是由美国人提出的。目前,对于重点关注中国海洋问题的智库,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只有极少数是欧洲的。这些智库的言论只有极少数是客观公正的。在这些智库中,其研究人员很少有研究海洋法、甚至于国际法的专业人士,而是多来自军队。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安全、地缘、战略等问题,因而多多少少带有有色眼镜,觉得中国是潜在的对手。其言论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导。从这一角度讲,退出公约是不明智的。即便有些条款的适用对中国不利,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同样不可忽视。附件七(仲裁)只是公约的一小部分,是零头的零头。退出公约将无视其余400多条为中国带来的利益,因而是因噎废食的。除此之外,即便是对中国不利的条款同样是可以规避的。中国无需时时处处效仿美国在海洋法领域的所作所为。”
“既然有人预断南海断续线是中国的权益主张,那么,它未来也可能是中方与有关国家的划界主张,如果仲裁庭针对南海断续线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定或要求中方澄清,均属介入海洋划界事宜。若此,仲裁庭又向越权与违法的泥潭迈进了一步,仲裁庭及其仲裁裁决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工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8条第1款确定的属事范围,是仲裁庭管辖权的固有限制。领土主权争端,即使仅为附带性或辅助性的,其结果的确定性不应由仲裁庭管辖,也不应作为规避管辖权限制的合法理由。本案中,仲裁庭的定性明显忽视了争端的构成标准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8条第1款的属事管辖权限制。仲裁庭只能审议菲律宾所提及的中国法案或文件本身,而不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全面主张。海洋权利资格并不由公约所完全规定。中国在南中国海海洋权利资格的其他法源,本身不属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事项。仲裁庭只能将此认定为一项事实,并且承认中国的主张符合历史性权利规则,才能有限考察历史性权利规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定条款相重叠和冲突的关系。”
南海仲裁“诡异之处颇多”,菲律宾精心包装的诉求看似单纯,实际上蕴含着极其险恶的用意,是以打压中方行使主权、伸张菲方主权主张为目标;而仲裁庭却装聋作哑,将明显不是《公约》适用、已被中方排除强制解决程序的争端送入实体审理阶段。菲方称将与中国争端的特定部分提呈司法解决有助于两国南海复杂争端的解决,这是在误导舆论。菲单方面强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不但不利于缓解南海冲突,反会加深两国间的误解,破坏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相互信任。
“如果说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会利用“司法能动主义”理论和实践试图超越解决争端的职能,那么国际仲裁应把管辖权严限于当事双方协议提交的争端范围,不应也无必要扩大管辖权。这是因为仲裁的临时性决定了其裁决的目的仅是解决特定争端,并不具有通过裁决实现社会建构的功能。而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明知中方的一贯立场是通过双边谈判协商方式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争端,明知中方不参与仲裁程序、不接受仲裁裁决,明知对菲方诉求的裁决起不到任何推动解决中菲争端的作用,却贸然行使管辖权、推进仲裁程序,这是对国际法治基本原则的破坏,是“司法”者僭越“立法”的职能,事实上剥夺了当事一方的意愿和权利。”
“由于中国坚持不参与、不接受立场,不可能自己指定仲裁员,而日本籍国际海洋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并没有回避,缺少合理性和正当性。他首次指定的斯里兰卡籍仲裁庭庭长品托的妻子是菲律宾籍,后由其自行辞职,随后指定的仲裁庭庭长门萨在2013年5月经加纳提名刚被任命为仲裁员,包括其在内有四名仲裁员是国际海洋法庭的前任或现任法官,尤其门萨和沃尔夫鲁姆一贯主张扩大国际海洋法法院和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海洋法庭的分身。当仲裁庭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投票表决时,“代表”中国的仲裁员并没有为中国说话。荷兰籍仲裁员松斯几年前公开撰文认为岛礁的法律地位问题与主权和划界问题不可分,这次却出尔反尔。这些反常表现在国际仲裁中极为罕见,不免让人对仲裁庭及其成员组成的独立性、正当性和透明性产生怀疑,从而削弱仲裁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中国已按照《公约》规定将海域划界等争端排除强制仲裁,中国拒绝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仲裁有坚实的法律依据,被强行推进至今的南海仲裁“极不明智”。 菲律宾和美国指望通过强制仲裁改变中国立场“纯粹是妄想”。事实上,菲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已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坚决的主权表态和主权行为。”
“仲裁庭未能在基于事实的客观基础上判断菲律宾诉求所掩盖的真实争端。海洋地物的地位与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密切相关,而仲裁庭没有认识到南海问题的根本性争议是主权问题,对南海海洋地物地位的判定,只有在相关主权问题解决后才可能给予合理的解答。”
“中菲一系列双边文件和中菲均参加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南海争端的共识,构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1条规定的“协议”,并排除了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仲裁庭以中菲之间的双边文件和《宣言》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为由,认定中菲之间没有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议”,这是对“协议”含义的曲解,忽视了合意行为本身即可构成“协议”,有悖《公约》相关条款的通常含义和立法精神。”
“国家同意对强制性仲裁来说必不可少,《公约》的强制性仲裁及其他强制程序均应严格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南海仲裁庭必须首先保证其管辖权不存在任何疑问,才能进入实体问题审理,否则裁决不可能有效。”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应该退场。仲裁庭临时组建,存在偏袒一方的嫌疑,对国际法的权威、对国际司法机构的信誉都将是巨大的伤害。”
1.2013年1月22日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五人临时仲裁庭,选定常设仲裁法院作为该案的书记处。此后,仲裁庭和菲律宾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
2.2013年8月1日
中国政府重申不接受菲律宾提起仲裁的一贯立场。2014年12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中国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立场文件指出,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调整范围,仲裁庭无权审理;中菲达成了以双边谈判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和《公约》;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各国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3.2015年10月29日
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裁定对菲律宾提出的7项诉求有管辖权,对其他诉求的管辖权问题合并至实体问题阶段一并审理。这一裁决受到多国海洋法学者质疑,国际法学界担忧仲裁庭擅自扩权越权可能创造危险的先例,破坏《公约》的整体性和权威性。许多专家指出,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无助于争端的化解,反而只会激化矛盾。与之相比,中方所主张的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才是正道。
❶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
❷关于中菲“南海仲裁案”中岛礁法律地位仲裁事项的初步研究报告
《中国国际法年刊 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专刊》作为国内唯一一本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法律专刊,由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法律出版社出版,定价:72.00元。该书即将于7月中旬限量上市,如有需要读者可通过拨打010-63939684或者添加微信号huanglinjia101与该书责任编辑黄琳佳女士取得联系,问询具体征订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