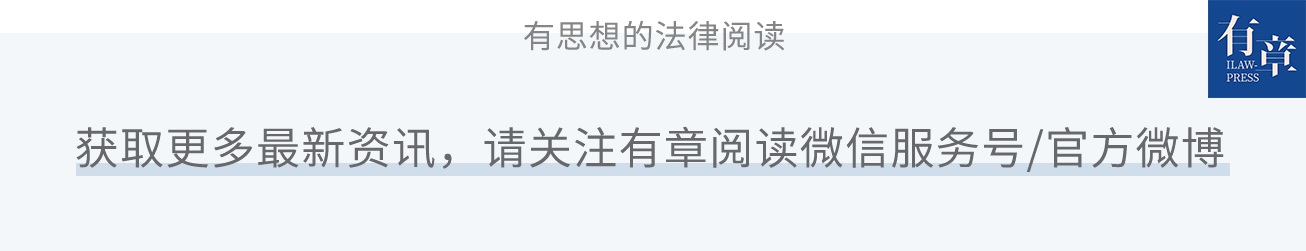梁文道:
节选自《读者》一书
如果篇幅不是那么有限,我实在很想在自己办的读书杂志里开个专栏,广邀各方名家轮流谈一本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经典,比如说让一位教文学的大教授承认他其实从未看过《红楼梦》;请一个自认是“看不见的手”底下玩偶的经济学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只言片语。这个灵感来自“英国钱钟书”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某本小说(我只能说“某本”,因为我从未看过任何一本他的小说)。他在书里设计了一个游戏,叫做“羞辱”,玩法是让一群知识分子在饭桌上趁着酒意轮流忏悔,说出自己没有读过的经典,谁说出来的名字愈经典谁就愈无耻,谁愈是无耻谁就赢了。听说那场游戏的最后冠军是个承认自己没 看过《哈姆雷特》的英国文学教授。我又听说美国学术圈子里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
去年横扫法国知识界的畅销书《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终于在万众期待的盛况下译成英文了。直到执笔这一刻,我还没收到这本书,但是我绝对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我一定会把它由头读到尾的。什么书都可以不看,这本书不行;因为只要读了它,以后别的书就大可束之高阁,我就能够专心一意地写书话骗稿费了。然而,这真是一本实用的指南吗?虽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个指南,虽然这就是它大受欢迎广获好评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看过它,你能确定它是本怎样的书吗?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素质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李维史陀讲课,就连福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学长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地铁里看《词与物》吗?当然不是因为它好看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叫人爱不释卷。重点在于要让别人看见自己正在读福柯的新书,正如穿衣服必须穿名牌,读书也得读名著。只不过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调,牌子不可轻易外露;读名著则要高扬,封面一定得让人见得到。”或问:“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拿本福柯的新著,何不干脆捧读福楼拜或者黑格尔”?学长又说:“笨蛋!潮流呀!都什么年头了,还看黑格尔,一来那些知识美少女会嫌你老套,二来那些没知识的美少女则根本不知道谁是黑格尔。至于福楼拜,人家可是法国的曹雪芹,你在地铁读《红楼梦》岂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没文化呀!”
我又接着问:“我见过一些英国人会用特制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么,这是不是因为英国人比较踏实低调?”学长嘿嘿一声冷笑:“低调?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调的书。你以为那些小羊皮套里藏的是什么?说不定是本三流通俗爱情小说,更说不定是个超淫贱黄书呢。难得他们看得血脉贲张,还要装出一脸严肃绅士状。所以说,英国人比法国人更无耻。”
“以貌取人”,英文的说法叫做“凭封面判断一本书”,无论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人非圣贤,有谁不好美貌呢?再说,要是不从封面判断书的好坏,不凭封面去吸引客人在书海之中拿起一本书,封面又有何用处?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很长一段的日子里,洋书是没有封面的,甚至不装订,就是一堆纸零零散散地送到书店去。那时候书还不多,顾客上门都早有目标,知道有什么新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客人们挑好了书,再选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连上头印的字款也随自己喜好,叫书店师傅替你完成装书的最后手续,结果就是你的私家藏书了。那是买书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书数以万计,还有哪家书店能够担起这种手工作坊的细活?还有谁能不“凭封面判断一本书”呢?书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书皮学”。以貌取书只不过是这门学问的幼稚园阶段,它真正的内涵是让人单靠书皮就“读懂”了一本书。“书皮学”本是大学时代我们拿来嘲笑人的话。一个家伙平日看起来是个博览群书的鸿儒,谈什么书他都能侃上两句,似乎无所不观。但一再追问,却又顾左右而言他,从一本书扯到另一本书,表面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实则绝不深入,永远在表象上徘徊。遇上这种人,我们就称赞他“精通书皮学”。
“书皮学”所以可能,《蒂封庭》是因为现代出版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总是想尽办法让读者不用真个看书。例如封面,一定会用最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一定会有夸张的名人推介 以及书评精句,至于作者介绍更是绝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还能对这本书产生最直观的实感)。若是学术书籍,那么书皮学的依据就更丰富了,比如索引和参考书目,内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和感受这本书的虚实。一部自称卓有创见的《文心雕龙》注释竟然只列了十来项参考书,连人家说过的东西都看得不多,你说它能多有创见呢?一本陶渊明论要是附有日文书目,这就说明作者对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不至于一无所知了。懂得这种种窍门,懂得从封底的有限讯息由小观大见微知著,“书皮学”的门径就算是开了。今天治“书皮学”又比我们当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联网的诞生。就拿“亚马逊”来说吧,上头起码有一半的书可以让人饱览封面封底。看完这最表层的 “书皮”,你还可以翻看目录,要是在目录遇上有趣的关键词,你 更能键入那个词,搜索有它出现的页数,速读几页。原来是吸引人买书的技术,落在“书皮学”行家手中,就成了“读通”一本书的利器了。
再说那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据知作者皮尔·巴雅(Pierre Bayard)是个有功底的教授,写作的态度很认真,而且这本书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实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读书但又要谈书”的现象和历史。巴雅发现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过书皮学的家伙,其中更不乏歌德这等级数的名人。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去谈一些他们根本没看过的书,甚至批评它们呢?这是不是种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还有许多作家学者喜欢公开表示自己从未读 过某本书,同时还保证以后也绝对不会碰它,然而又能洋洋洒洒 数千言地陈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这是种最理直气壮最坦白的“书皮学”,据说巴雅也有他的分析。这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我连见都没见过,又怎么知道它的内容梗概呢?这就叫做“书皮学”了,你上网查查就懂了。
我们应该老实承认,我们大部分我们说要看的书,或者看过的书,其实我们不一定会把它们由头到尾看完。比如说拿我们做这个节目来讲吧,我每个星期给大家选三四五本书,问题是这些书要怎么选出来呢,我要从更多的书里面选出来,那些更多的书,如果我们连看都没看过,我怎么去选择呢?所以我必须把一些我候选的书,比如人家寄给我的书,或我买的书,我都要先要翻一翻,然后选一些我觉得能够在节目里面介绍的书。那些被我翻过的书,你说那些书,我到底是有看过,还是没看过,你说没看过,但起码你翻过,略知一二,你说你看过嘛,但其实你又不是真的把它从头到尾透彻地看一遍,这个情况是个很普遍的情况,然而很多人仍然觉得我们应该把一本书由头到尾读完才算是对得起书,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种独特的技巧。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它的英文版的书名《Howto Really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他的作家叫做HenryHitchings,亨利·希金斯,是一个英国相当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历史评论家。他这本书,其实是在回应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曾经在这介绍过另一本书,那个书叫做《不用读完一本书》,现在这本书加了“真的”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介绍那本书是法国学者巴亚德写的书。那本书与其说真的是在教你怎么样不用读完一本书,又可以谈论它,倒不如说它其实是在讨论一种文化史跟书籍史的观念。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一本书,我之所以会讨论到它,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很重要,而是这本书上在文化史上面的,在某些知识里面的独特地位,所以我们要了解一本书,光是看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他的脉络,他跟其他的书,他跟同时代的书,前前后后那些书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年我介绍的那本书,并不是真的是在教你取巧的,不用读完那本书就能够说它,而是通过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里面去谈一种文化观念。然而我今天介绍这就不一样,它是要真的教你,怎么样可以不用读完一本书,也能够去讨论它。
现在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你不能老实承认自己没看完一本书呢?他就提到,就是因为聊书是一项社交活动,而他们英国人认为辩论是他们很喜欢的一项活动,辩论能够接近真理,接近辩论的日常聊天都很有意思,而如果这种辩论或者聊天牵涉到书的话,就格外的有教益。因此我们需要常常在聊天里面提到一些书。提到那些书的时候,你又不可能完全读过,这时候你就要装了。然后这里面,他就教了很多的技巧,比如说他说平常你去形容一本书的时候,或者形容一个作家,你与其说他很无聊,不如用另外一个字眼,看起来会比较象话,那四个字就叫做这本书“平庸乏味”,看起来好像很专业。
然后他又提到,但是问题我们要了解,并不是所有的书你都应该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尽管有一些书。比如说像19世纪一些大小说家狄更斯等等,这些作家很多现代人都觉得是必须要读的。但是大部分又往往不会读,这时候聊起来又不显得无知,怎么办?他提供一个秘诀。他说当你提到这些你没看过这些经典名著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人家谈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最出名的情节,相反的,你要恰到好处的提起一些次要的角色,例如说《咆哮山庄》,也有人译作《荒凉山庄》里边,你可以考虑一下特威多普这位老先生,他是个次要的角色,他绅士师范十足,经营一家舞蹈学院,惋惜英国礼俗的没落,批评英国人是只会缝缝补补的民族。
他说你熟悉这些人物,一说起来,人家觉得你还真看过这书,里面这么次要的角色,你都记得住,但其实你根本没读过它。但是他又主张,我们要小心一点,有些书你真的没看过了,你说话会出事。例如说《古兰经》,他就说到现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伊斯兰宗教文化,还有极端势力的争论,特别敏感,特别多。这时候我们讨论《古兰经》的时候,就应该格外慎重,在写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收起了他嬉皮笑脸的态度,相当严肃。他就说到,只要有人宣称《古兰经》怎么怎么讲,你就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人家引述关于《古兰经》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
……
但是我们的作者就讲了长篇大论,又教你怎么谈普鲁斯特,又教你怎么谈莎士比亚。可是你看得出来,他每一章都用心良苦,他是真的希望他的读者,不止是看了他写这些就出去瞎掰、瞎砍,而且还是真的应该把他们看完。尽管到了最后,他都承认了,他说其实我介绍那么多书里面,有一本我是没看完的,你们猜猜看,是哪一本?先不讲这个,我再说到,你要谈一些你没看过的书,这像什么状况呢?这里面就提到,他说这其实就是个说谎,这种说谎就等于股票经济人永远跟你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于卖房子的告诉你说这区的房价看涨。然后他就说像这种唬人的方法,其实就像赌扑克牌,赌扑克牌重要的永远不是你手上有一张什么好牌,而是你让别人觉得你有一张什么样的好牌,不过到了最后,他就提到,只有对着一种人的时候,你千万别胡来,那就是念哲学的人,因为他说我们这些念哲学的人,是对这种谎言特别感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