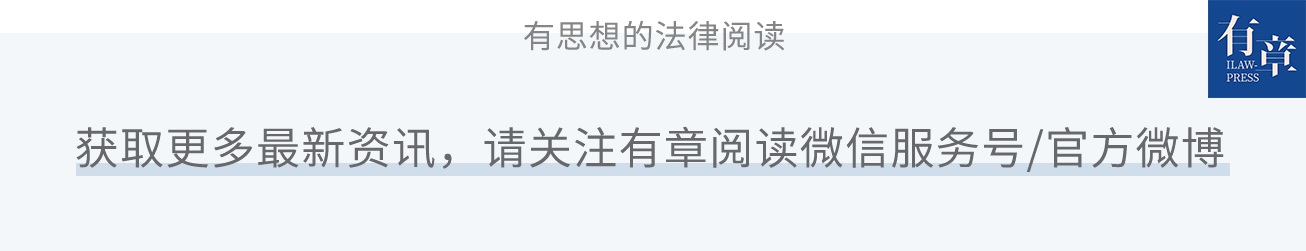本期推送从多个维度解读正义,与此日历相得益彰,感谢作者授权,敬请关注!
刘文科
法律出版社编辑
目次
一、诗歌中感受正义之美
二、神话中感受正义之美
三、悲剧中感受正义之美
四、中庸中感受正义之美
卷帙浩繁的古罗马经典文献《学说汇纂》(Digesta)在开篇的第一卷第一章摘编了乌尔比安在《法学阶梯》(institutionum)中的一段话:“致力于法的研究的人首先应该知道‘法’(ius)这个称呼从何而来。法其实来自于正义:实际上,就像杰尔苏非常优雅地定义的那样,法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
乌尔比安在《规则集》(regularum)中还说:“正义是给每个人属于他自己法律情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Institia est constans et perpetua voluntas ius suum cuique tribuendi)
Domitius Ulpianus
乌尔比安的这句名言,被后世法学家奉为真理——无论是伟大罗马皇帝优士丁尼在他不朽的教科书《法学阶梯》中,还是近代自然法的鼻祖格劳秀斯在狱中为他的孩子所撰写《荷兰私法导论》中。西方语言中,正义与司法同为一词(justice)。从动态的角度而言,司法乃是实现正义的过程;而从静态的角度观之,正义无非司法的终极目标。
Gustav Radbruch
千百年来,人们陷在正义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多少隐喻着正义之于人具有某种美的属性。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哲学》中说:“正如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法律也需要形象的表达方式:语言、表情、(有特色的)服装、符号,建筑等。”
其实,古希腊的柏拉图早就将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
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说:“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代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
Jacob Grimm
而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学生、格林兄弟中的哥哥雅各布·格林为此专门写就长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开篇说:“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像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
我国族亦以诗歌体将法典传世。上古西周法典《吕刑》中不乏这样的词句:“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
而唐朝的法律家张鷟用对仗工整、韵律铿锵的四六骈文体使盛世的法律编例得以传世。在他编撰的《龙筋凤髓判·中书省》中,针对王秀不服判决,请以从犯减轻处罚的诉讼要求,张鷟作了如下优美的批语与解释:“张会过言出,驷马无追。王秀转漏于人,三章莫舍。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
就连诗人白居易也愿意用诗歌的形式写些判词。《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六和卷六十七收录了百余则“书判”文字,人们称它为“白居易甲乙判”,这是一批模拟公堂断案而制作的“判决书”。
其中一则:“亲以恩成,有仇宁舍?嫁则义绝,虽报奚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萑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着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白居易用如此繁复规整的辞藻宣讲礼教,可谓用心良苦。
神话的逻辑形式是自言自语;神话的修辞程序与叙事、而非论证相关;神话的借以实施的象征中介是形象,而非理式;神话的认识论意图建立于事实、而非证实的基础之上;神话如镜子般映射出来的本体参照是世界整体,而非某一逻各斯自然衔接之物的特殊事实。([法]马特:《柏拉图与神话之镜:从黄金时代到大西岛》)
Ἡσίοδος
远古时期,东西方的民族都善于用神化讲述正义。古希腊的赫西俄德是讲神话的高手,他留给后人的《劳作与时间》既是神话,也是诗歌。在这首神话诗歌中,有一段是关于正义女神狄刻的故事:
还有个少女叫狄刻(ἡ δέ τε παρθένος ἐστί Δίκη),
宙斯的女儿,
深受奥林波斯神们的尊崇和敬重。
每当有人言辞不正,轻慢了她,、
她立即走到父亲宙斯、克洛诺斯之子身旁,
数说人类的不正心术,
直至全邦人因王公冒失而遭报应。(256-261)
在这几行诗中,正义女神狄刻被称为少女——παρθένος,这个希腊语单词也用来形容最初的女人潘多拉和处女神赫卡忒。但是,诗人赫西俄德开诚布公地指出,贵族王公根本没有认清狄刻的真正身份,迟早要为此吃苦头。在他们愚昧的眼里,狄刻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少女,轻易就能被打败,乃至被逐出城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柔弱的少女狄刻背后,不仅有宙斯这个绝对权威的靠山,可以自由出入天庭,就是行走在人间时,也并非孤身一人,而有好些同伴和帮手。(吴雅凌:《劳作与时间笺释》)
正因如此,也有人说,“少女”并非是指纯洁无瑕,而仅指狄刻女神未婚,因而在受到冒犯时,没有丈夫保护,只有求助父亲。
神话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叙事时间的遥远性和叙事者空间的奇特性而尤为明显。借某个陌生的叙事者之口说出,目的在于通过特殊的模仿影像,显现那浮现于不可见的诸种存在之整体。([法]马特:《柏拉图与神话之镜:从黄金时代到大西岛》)《高尔吉亚》载,在神话中克洛诺斯(Κρόνος)统治的时代,活人审判活人,时间是被审判者死去的那一天。
但是审判者很难真正行使正义,因为他们往往被美丽的外表或华贵的服饰所迷惑。为了重建正义之理,宙斯决定,人死后由灵魂接受审判。最后的审判将摒弃一切外在的东西,而审判者也同样是死去的人。
宙斯派遣自己的三个儿子——米诺斯、埃阿科斯、拉达曼特在草地中心审判亡灵。草地位于十字路口,其中有两条竖直的路,一条通往幸福岛,另一条通往塔尔塔罗斯。这两条路代表天和地。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水平的路,从亚细亚来的死者要接受拉达曼特的审判,从欧罗巴来的死者接受埃阿科斯的审判。米诺斯作为最后的审判者,为死者指明最适合他们的道路。
神话中,正义的地形图处于灵魂四个方向的均衡之中。柏拉图的注释者普罗克洛斯认为,宇宙的正义呈现为“5”,他在《王制注疏》中说:“审判处就位于天地之间,这不是因为它是唯一拥有审判者的地方,而是因为中心永远适合审判者。遵照法则,审判者把最初的与最终的归同平等。就好像数字‘5’象征正义,因为正义在9和1之间保持中立。”
在恐怕是《诗学》最著名的段落里,亚里士多德如此定义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这样解释“怜悯”:“一种由于落在不应当受害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或者因其痛苦的、想来很快就会落在自己身上或者亲友身上的祸害所引起的痛苦情绪。”
Aristotle
而他对“恐惧”的解释是:“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人们并不畏惧一切灾祸,例如自己将成为不义的或蠢笨的人,而仅仅畏惧足以导致很大痛苦或毁灭的灾害,只要这种祸害不是隔得远,而是近在身边,迫在眉睫。”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就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从戏剧的角度而言,我们观看悲剧是为了获得激情而非湮灭激情。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话来说:“诸如怜悯、恐惧、神灵感应,这些会强烈出现在某些灵魂那里的激情,也存在于所有灵魂中。只是因或弱或强而有所区别。”
然而,悲剧也许意欲像疫苗那样起作用——在事实治病之前,诱发某种疾病之貌,行疏泄疾病之实。那么,我们去看《奥赛罗》,是为了防止我们患上嫉妒之疾,而非治疗我们已然感染之疾。([美]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
加缪的悲剧《正义者》中,本来是谋杀沙皇皇叔的恐怖小组,是正义为他们的谋杀赋予了崇高的意义。恐怖小组中唯一的女性多拉说:“我仇视专制政权,也知道我们别无他法。然而,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做出这种选择,却怀着忧伤的心情坚持,这就是差别。我们是囚徒。”
Albert Camus
加缪自己在谈论悲剧时说:“仅有反抗,不足以成悲剧;同样,仅表现神的秩序,也不足以成悲剧。反抗和秩序,两者必须并存,彼此支撑,相互借力。”借用他笔下的多拉的话来说:“有了矛盾,死比生容易,容易千百倍。”
西方文学史中不乏法律题材的戏剧,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一报还一报》。但是,正义之美在于悲剧。在《安提戈涅》中,“神通过具体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的因果机制显明正义法则”。(肖厚国:《古希腊神义论:政治与法律的序言》)
按照加缪的理解:“在悲剧中,相互对立的力量,都同样合情合理;反之在情节剧和正剧中,只有一种力量是合法地。……在前者中,每种力量都又善又恶,在后者中,一种力量代表善,另一种力量也不错。”如此说来,安提戈涅有道理,但克瑞翁也不错;普罗米修斯极有道理又没道理,无情压迫他的宙斯也行之有据。
可以说在一定限度上,所有的人都是对的,于是,“一个人因盲目或者激情,无视这种限度,自投灾难,才使他以为独自拥有一种权利获胜”,这就是悲剧的主题,也是悲剧之于正义的审美的所在。
“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括。”(ἐν δέ δικαιοσυνη συλληβδην πασ᾿ ἀρετὴ ύι.)古希腊的哲学家将正义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关乎人的行为:“正义是正义的人在选择做正义的事时所表现出的品质。”(《尼格马可伦理学》)
因而,古人意在探求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是正义的。就像年轻的赫拉克勒斯在孤独中思考未来的生活道路,遇到“美德”与“恶习”两个女子,最终他摆脱恶习的有人承诺,选择美德的艰难道路,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提醒佩耳塞斯:
佩耳萨斯啊,听从正义,莫滋生无度。
无度对小人物没有好处,
显贵也难以轻松承受,
反会被压垮,遇着惑乱。
走另一方向的路好些,通往正义。
正义战胜无度,迟早的事。
傻瓜吃了苦头才会明白。(213-218)
“正义战胜无度”(δίκη δ᾿ ὑπὲρ ὕβριος ἴσχει)。在古人心目中,正义和无度相对立。
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中说:“正义显然是行不正义与受不正义的对待之间的适度:前者得的过多,后者则得的过少。”这便是正义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在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在于成几何比例,“不正义或者是过多,或者是过少”。矫正正义遵循的是算数比例,“正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违反意愿的交易中的得与失之间的适度”。
其实,在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念中,“正义”和“平分”有着密切的联系。“τὰ δίκαια”是指“正义”,“δίχα”是指“平分”,“δίκαιος”是指“正义的”,“ δικαστής”是指法官(即“正义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找法官就是找中间,人们的确有时把法官叫作中间人,因为找到了中间也就找到了正义。所以正义也就是某种中间,因为法官就是一个中间人。”
作为一种美德的正义,不是先天的自然禀赋,而是实践的。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运用理性的良知,选择中庸之道。因而“来自于正义”的法亦是寻求中庸之道。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下,古代的私法致力于培育人的这种实践智慧与理性的良知。
《法学阶梯》中讲述:
“如果某人当他人不在时管理该人的事务,就产生双方相互间的诉权,称无因管理之诉,本人对管理人得提起正面诉讼,管理人得对本人提起反面诉讼。显然,严格来说这些诉权并不根据契约发生,因为它们仅在一方未受委任而自动地管理他方事务时发生;因此,其事务受人管理的本人,纵然不知情,也负有义务。
只是为了考虑到实际效用而被认定的债务,使不在的人,不致由于当初急需动身未及委托他人管理其事务,而其事务无人过问。无疑,如果管理人不享有诉权,使本人偿还他在事务上可能支出的费用,任何人也不会去照管他人的事务的。另一方面,以对于本人有利的方式管理其事务的人,既然得使本人负担义务,同样他对本人也负有提出管理状况报告的义务。”(I,3,27,1)
伟大的罗马法中贯穿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它教会了人们平等:一方不能所得过多,另一方也不能所失过多;在某一方面获得,在其他方面丧失。双方的得失总是大体相当,从而达致一种适度的状态。也正因如此,法才可以被称为一种“技艺”——达致适度状态的技艺。
毫无疑问,为了达致这种适度状态而传授这种技艺的人,一定是首先就是气韵温和的,这一点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优雅文字中可以得到体会。也只有能写出这样优雅的法学著作的罗马皇帝,才能“向有志学习法律的青年们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