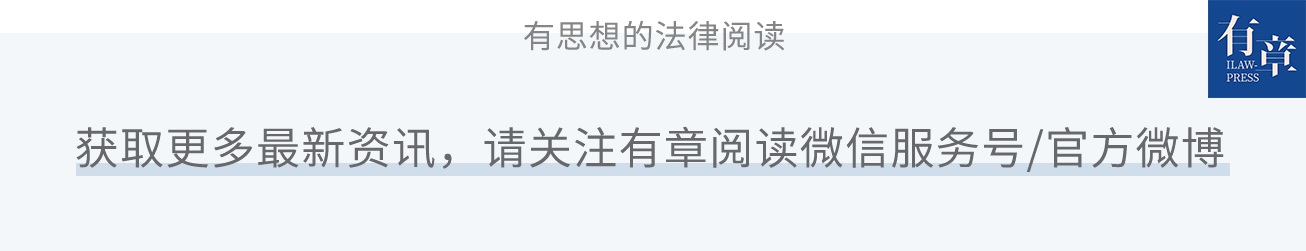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十八世纪的法国,是出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和思想家的岁月和国度。有了让·雅克·卢梭先生和《社会契约论》,这可谓是法国的光荣和人类的幸运。卢梭先生虽然只活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在那时恐怕也是高寿了吧),但他提出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犹如一个特殊的人文保健因素,为后世指出了一条有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因此,《社会契约论》具有解决启蒙性、根本性、方向性问题的巨大功用,成为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还包括其他学科)的学子必读和应读的经典,特别是对法律人发挥着巨大的思想影响,是形成正确的法治观的重要思想营养,可见这本经典著作具有巨大和长久的影响力。”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奠定理论基础,其"主权在民"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
《社会契约论》曾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理论指导,梁启超也追随其步伐将《社会契约论》一步步向中国传播;与此同时,在伦敦流亡的孙中山,即使在靠资助度日的艰难条件下,依然把仅有的钱购买《社会契约论》研究;毛泽东早年曾悉心研读《社会契约论》,了解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潮,而这正是他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基础。
2014年习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法国,向媒体公开自己的书单,重点推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及《社会契约论》是思考和研究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著作。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在费城获得批准,从此,美国踏上了平等、民主、法制的发展之路。而它的起源,正是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掀起的民主启蒙思潮的《社会契约论》;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至今,单在法国就有150多位学者在专门研究卢梭与《社会契约论》。
1985年,法学家费孝通呼吁全社会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因其中的民主理论是中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基础。未来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离不开这本散发民主光辉的神圣著作。
钟书峰 译本

重译经典《社会契约论》的理由
我心中设定了经典重译的“三不”原则,即不超越、不重译、不出版,并为此而推却了许多可有可无的应酬,少喝了许多价格不菲的假酒。
——题记
钟书峰
收到委托翻译出版卢梭名著《社会契约论》的合同书后,迟迟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等了许久的对方在两个月后通过电子邮件催促我尽快签合同。迟迟未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一直无事找事地苦苦追问:何谓经典?它是不是经典?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值不值得重译?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经”的其中一个含义,即指“经典”。“典”,指“典范性书籍”。“经典”,作为名词,既可以“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也可以“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作为形容词,或者指“著作具有权威性的”,或者指“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这太啰唆,不如网络词典的解释来得简洁: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按照上述解释,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毫无疑问是经典,至于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的哪些中外作品属于经典,或许会有一些争议。
鉴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最早于西方称为经典,因此,作为略懂外语的穷书生,不能免俗而从外语中寻根找据。英语的“classic”(经典),源自“class”(课堂),最初指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书本。在西方,数个世纪以来,古罗马、古希腊作品都是其学校课堂的基本用书,因此,“经典”后来就引申为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在文艺复兴后,该词又指受古代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作品的风格、思想的影响或者启发而创作的作品。再到后来,“经典”指任何伟大作品。从以上所述可见,“经典”与“classic”的互译,简直是绝配。
虽然《社会契约论》不是创作于古代,但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对卢梭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契约论》可以称为经典。但是,若仅以此为据,认定其属于经典,显然既荒唐又滑稽。
经典,必定是文风与构思值得后人学习的作品。虽然我早已拜读过卢梭名著《社会契约论》,但只是作为政治法律书籍进行阅读而已,因此,当听说出版社是把它作为文艺作品而策划翻译出版时,让我大跌眼镜。坦白说,当时心里不免很小看组织策划出版《社会契约论》的有关人员。但是,随后为翻译此书而逐渐展开的资料收集过程所反馈的信息,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不过这次是对自己大跌眼镜:西方一直都有相当多的学者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视为法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认为该著作用词精炼、行文简洁、文笔优美、构思精当。例如,有西方学者就撰文指出,该著作中的名句“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法文: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英文: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就是卢梭反复琢磨修改的结果。其最初的法文是“L’homme est né libre, et cependan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译为对等的英文是“Man is born free; and yet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或者是“Man is born free; and nevertheless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译为对等的中文是“人人生而自由,然而却无处不在枷锁中”,或者是“人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这显然不够简洁。只要有心把通称为《日内瓦手稿》的《社会契约论》初稿,与其定稿出版物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长达十多年的创作中,卢梭是如何字斟句酌的;只要读一读《社会契约论》,就知道它是多么适合作为大声朗读的读物的;只要不是附庸风雅地阅读《社会契约论》,就可以体会到其环环相扣的谋篇布局耗费了卢梭多少心血。
经典,必定是具有巨大历史影响的作品。这种影响,具体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18世纪以后的各国政治,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具有重大影响,其《人权宣言》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美国的独立战争同样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其《独立宣言》及其宪法的某些词句,甚至是直接英译自《社会契约论》的文本,更不必说其他国家。第二,对后世人物的影响,如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直接引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杰佛逊、罗尔斯等政治思想家无不受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鉴于这方面的论述与介绍,实在是多如牛毛,拙文不再具体赘述。
经典,必定是思想与观念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一名著改造了当时的人们所使用的“权利”“自由”“政府”“主权”“公民”“法律”等诸多基本概念,赋予其全新的更为准确的含义,让我们如今的政治法律论述更为精确妥当。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共意志”(法文volonté générate,英文general will),因其原创性而让后人把它等同于卢梭的名字本身,提到“公共意志”就会想起卢梭本人,提到卢梭就会想起“公共意志”一词。诸如此类的基础性概念很多,限于篇幅,也不再一一赘述。其实,卢梭名著《社会契约论》的贡献,更主要的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思想,其提出的社会契约思想,不但改造了社会契约这一概念,而且发展了社会契约这一思想。由于它不同于在此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契约思想,也不同于在此之前的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契约思想,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从概念到思想,都具有原创性。此外,卢梭对“人性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等划分政治思想派别的基本问题,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回答,从而使其思想自成体系。
窃以为,一切经典都是当代经典,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历史一样。
倘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于中国,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法治等方面的建设,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至少在中国就不能称其为经典,因而不值得重译,不值得出版社浪费纸张出版,更不值得中国读者阅读。中国的政治、民主、法治等方面的建设,一直是一个令人心情沉重的话题,也一直是一个令人充满期许的话题。《宪法》第2条第1款白纸黑字地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没有考究,这一规定究竟直接源于何处,但我知道,它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人民主权理论,简直是一模一样,而且我们都知道,文本上的宪法规定不等于现实中的宪法规定。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证明这一点,因此,拙文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必多言,我只是心中有一个期盼: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经推动了近现代中国走向进步,但愿拙译的《社会契约论》仍然可以推动当代中国走向进步。
据学者考证,最早知道卢梭并阅读《社会契约论》的中国人,可能是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1878年即光绪四年的4月3日,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乐苏”(即卢梭)的名字,认为他和“华尔得尔”(即伏尔泰)“著书驳斥教士”。稍后,先哲黄遵宪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也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黄遵宪知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能源于日本人中江兆民于1882年所译的名为《民约通义》的首个中译本《社会契约论》。自该译本问世后至今,已经有很多中译本,但学界均普遍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兆武译本是最权威的译本。不瞒诸位,早在20世纪90年代于西南政法学院求学时,我在当时藏书最丰富的政法院校图书馆拿起何译,看了几眼就根本无法看下去,原因无他,感觉伟大的哲人卢梭怎么写得像他的名字的谐音一样啰啰嗦嗦,甚至语句都不通顺呢?后来,充满传奇色彩的邓又天老师,带我到据说当时只有院领导或者教授或者其他什么特别的人才可以进入的一个外文书库,以邓老的名义借阅了外文版的《社会契约论》后,才知道不能怪卢梭,而要怪何译。虽然拙译对何译以及其他译本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拙译从何译以及其他译本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何译等译本对拙译具有借鉴作用;二是何译等译本对拙译具有启示作用;三是何译等译本对拙译具有警示作用。因此,衷心感谢何译等译本的译者。



出版社方面是让我把英文版的《社会契约论》译为中文出版的。但是,在收集了几乎所有的中译本和从国外邮购了能找到的英译本以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英译本都存在诸多像何译一样不可靠的地方。因此,下定决心,学习法语,并又从国外邮购了几种法文版的《社会契约论》。上述邮购过程,让我对人民币在国外并未大幅升值而在国内却大幅贬值有了实打实的感受,让囊中羞涩的我备感荷包瘪瘪,但更痛苦的是翻译期间的艰辛付出,此处就不摆了,只想请诸位贤达看看以“Frontispice de l’édition de 1762”为源语版本并参考了其他法文版和以G.D.H.Cole英译本为主的众多英文版以及以何译为主的众多中文版的拙译,究竟有没有超越何译,并诚恳邀请诸位贤达斧正拙译,以便今后有机会再版的拙译所存在的败译、误译、漏译、硬译之处会更少一些。
当然,我心中是设定了经典重译的“三不”原则的,即不超越、不重译、不出版,并为此而推却了许多可有可无的应酬,少喝了许多价格不菲的假酒。虽然自信拙译并没有辜负上述信念,但是,不断发生的法治缺位的事件,令人痛心,作为法学博士的自己,不对,是作为人的自己,竟然未吭一声,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没有辜负上述信念。
钟书峰
2011年1月30日下午草于南粤鹏城2011年2月4日傍晚
改于南粤海城2012年4月4日晚上改于江西龙南
钟书峰 编
1、1882年,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又译“中江笃介”)中译本《民约译解》(只翻译了前言至第一卷第六章)在日本出版。 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民约译解》第一卷,题名《民约通义》。

2、1900年,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日译本而完整翻译的《路索民约论》中译本问世,后于1900年12月6日至1901年12月15日以《民约论》之名在《译书汇编》第一、二、四、九期上连载。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其单行本。

3、1913年,上海《大同周报》于当年5月4日、5月11日分两期连载译者署名为“兰士”的《民约论,又名政治之原理》(内容含《译叙》、《目次》、《引言》和第一卷前言)。
4、1918年,马君武以法文原著与托泽(H.J.Tozer)英译本互证,翻译的《足本卢骚民约论》中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5、1935年,徐百齐、丘瑾璋根据科尔(G. D. H. Cole)英译本《社会契约论》翻译的《社约论》中译本,编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出版。
6、1944年,卫惠林根据Hatier-Paul Lemaire & Hachette的法文版《社会契约论》翻译的《民约论》中译本,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7、1958年,何兆武根据法国巴黎奥比埃出版社法文版《社会契约论》,翻译的《民约论》中译本,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63年,更名为《社会契约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第2版。2003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第3版。据“译者前言”介绍:初版系“根据奥比埃(Aubier)版、摩·哈伯瓦斯(M. Halbawachs)注释本译出,翻译过程中对照了1827年菲尔涅(Furne)版《卢梭全集》本和比较通行的另外几种版本”;再版时,“又根据伏汉(C. E. Vaughan)本(剑桥两卷本,1962,及龙门一卷本,1914)和波拉翁(G. Beaulavon)本(格拉赛一卷本,1920)全部重校过”。

8、1997年,《华夏文摘》增刊分四期连续刊载署名“其林”(又名“赵小麟”、“艾仑”)之人根据贝尔(Lowell Bair)英译本和科尔(G. D. H. Cole)英译本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
9、2004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国政根据法国伽里马出版社1964年法文版《社会契约论》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2006年5月,该社又出版其精华版。
10、2004年8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陈惟和、张一江、宋文等翻译的《卢梭民主哲学》一书,内有《社会契约论》中译本。该译本未交待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
11、2006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华文编译的《社会契约论》。
12、2007年1月,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强翻译《社会契约论》英汉对照版。该译本“译者后记”称,系“根据Maurice Cranston的英文版本译出”。2009年12月,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
13、2007年6月,人民日报社出版罗玉平、李丽编译的《社会契约论》。
14、2007年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施新州编译的《社会契约论》。
15、2009年1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庞珊珊根据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英译本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
16、2010年1月,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克兰斯顿英译、高黎平依据该英译本翻译的《社会契约论》英汉对照版。
17、2010年10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乔坤、张静编译的《社会契约论》。
18、2010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笑语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该译本“翻译所依据的底本,是学术界通行的版本(1762年荷兰版)”。
19、2011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平沤根据巴黎嘉尼埃—弗拉玛尼翁(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1966年法文版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
20、2011年8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刘丹、宋淼翻译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译本。译者未交待该译本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
21、2011年10月,译林出版社出版陈红玉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译者未交待该译本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但从该书版权页注明的“书名原文: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字样以及“买中文版送英文版”的腰封而且所送英文版与科尔(G. D. H. Cole)英译本完全一致来看,似乎翻译时所依据的系科尔(G. D. H. Cole)英译本。
22、2012年3月,根据1762阿姆斯特丹版、1943奥比埃(Aubier)版等为主的法语原版,学习参考以科尔(G. D. H. Cole)英译本为主的英文版以及何兆武译本为主的众多中译版,钟书峰翻译《社会契约论》。
23、2012年4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戴光年翻译的《社会契约论》中译本(双语版)。该译本未交待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但从其双语为中英而且英译本与托泽(H.J.Tozer)英译本完全一致来看,似乎不是译自法语,而是译自托泽(H. J. Tozer)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