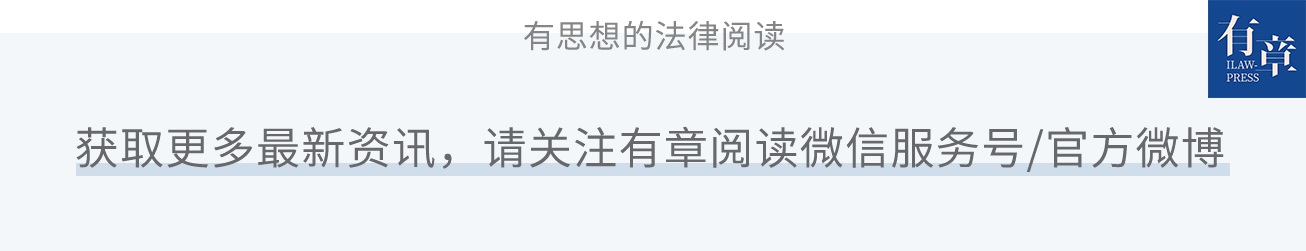2018年6月16日晚6点30分,“北大·德恒刑事法理论前沿系列讲座”第一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3会议室成功举行。
本系列活动由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主持。活动定位在纯粹理论性的学术活动,旨在推介和传播刑事法学界最新最前沿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交流平台,增进理论探索的影响力,为刑法学术传统的积累贡献绵力。
本系列活动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赞助支持,特冠名为“北大•德恒刑事法理论前沿系列讲座”。
本场讲座的主题为“故意的肯否之外——事实错误的第三种结局”,主讲人是台北大学法律学院蔡圣伟教授,讲座内容以蔡圣伟教授在2013年发表在德国刑法学者Frisch的祝寿论文集中的《故意既遂归责》一文为基础扩展而成。
评论嘉宾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钢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柏浪涛副教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王兆峰律师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博士、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程晓璐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韩友谊律师也出席了讲座。

车浩教授在简要介绍蔡圣伟教授的学术背景后,宣布讲座正式开始。
蔡圣伟教授认为,无论德国还是台湾,以往的理论皆主张,事实错误的法律效果无非阻却故意与承认故意两种,事实误认重大者,阻却故意,反之则成立故意,比如打击错误乃事实误认重大的情况,应当阻却行为人对实际受害者的故意,对象错误则属于无关紧要的事实误认,不妨碍故意的成立。
虽然早在百年前,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就认为,对象错误不阻却故意这一观点不甚妥当,亦即事实错误在刑法与民法中的处理规则应当保持一致,有必要将民法的错误理论适用到刑法中,使动机错误能够左右行为人故意的成立,但这一观点如今已少有支持者,因此事实错误的法律效果在通说中唯有上述两种而已。
针对通说的观点,蔡圣伟教授质疑道:
为什么在对象错误中,行为对象具体特征的误认并不影响故意的成立,而在打击错误时,行为对象的不同却会产生阻却故意的效果?
再者,行为人的故意在着手时即已存在,着手后无论事态如何发展,都不能再倒回来否定着手时的故意,通说动辄称故意阻却,道理何在?
依蔡圣伟教授之见,这是因为事实误认的法律效果除故意的有无外,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一方面承认行为人有故意,另一方面并不会因为行为人有故意,就一定会受到故意既遂的评价。如此一来,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也会随之变动。
按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构造,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审查方式是,先确认客观发生的事实和行为人着手时的主观想象,再查找可供适用的罪名,这个罪名的所有成文与不成文要素,即构成要件要素,都是判断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符不符合构成要件的标准。
客观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审查,是以这些要素来涵射客观事实,主观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认定,也是用相同的要素去考量行为人着手时的主观想象,只有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都符合系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肯定构成要件该当性。
按照这种理解,故意的内容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亦即行为人着手时根本不必认识到构成要件要素,而是只需要知晓那些能够符合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
不过,这种分离主客观认定的处理模式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之间总会有所出入。换言之,即使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先后通过了主客观构成要件的过滤,也不能径直认定行为人成立故意既遂,这是因为,在得出故意既遂的结论之前,还缺少一个主客观要件是否对应的审查环节。
以打击错误为例,行为人客观上杀死一人,主观上亦想杀死一人,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一应俱全,可即便如此,也还是难以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个中原因在于,主客观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对应的问题还有待解决,详言之,随意配对的主客观事实无法构建出故意杀人既遂的不法,只有充分对应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才能做到这一点。
以这种理解为前提,故意既遂的不法绝非主客观构成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还需要额外添加一个审查主客观构成要件是否充分对应的阶层,只有在客观构成要件、主观构成要件以及对应审查要件全部齐备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因结果归责于故意不法而承担故意既遂的刑事责任。
虽然通说在运作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完成对应审查的任务,但其方式却是将故意的认定和对应的审查合并处理,长此以往,司法者便会混淆二者的功用,导致断案的恣意。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主客观构成要件对应审查的具体操作中,究竟哪些要素是必须对应的,判断的尺度又如何拿捏?依蔡圣伟教授之见,主客观构成要件的对应审查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以立法者的指示为基准。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已通过文字表述显示出各个构成要件要素的抽象程度,比如,立法者将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对象限定为“人”,因此诸如人的具体特征、职业、身份等等,就都不是对应审查的重点,重点惟在于,行为人杀的是一个人。
同理,在包含选择构成要件要素的罪状中,立法者原则上认为每个要素都具有等价性,故误认此选择要素为彼选择要素者,便不会阻却故意既遂的刑事责任。
第二,以风险的描述为依归。抱着解决故意既遂认定的目的,德国有学者曾提出风险理论,具体内容是,故意既遂的成立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人能不能认识到客观上导致结果发生的风险。
但是,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风险的内容会随着描述角度的不同而发生转变,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描述的可操控性,比如在著名的“坠桥案”中,行为人欲将婴儿从高桥上推下,使之落水溺毙,但婴儿实际却是撞到桥墩而死。就此而言,人们既可以将风险描述为婴儿撞到桥墩致死的可能,也可以描绘成婴儿从高桥上坠落的死亡危险。
倘以第一种风险描述为准,行为人自然没有认识到婴儿会撞到桥墩而死,因此故意既遂实难成立,反之,若从第二种风险描述出发,行为人毫无疑问会知晓婴儿从高桥上坠落的死亡可能,故意既遂当然成立。为何相同的事实和理论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一言以蔽之,风险之确定是一个规范抉择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查明问题。
为弥补风险理论的漏洞,使风险描述的操控可能降至最低,蔡圣伟教授主张修正的风险理论。
该理论给出的方案是,让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互相牵制:司法者先选出客观事实和主观想象相重合的部分,并以这些相互重合的部分为基础描述一个新的事实,然后再从客观判断者的角度出发,审查这个被描述出的新事实能否构建一个不受容许的风险。
以“坠桥案”为例,假如行为人的主观想象为桥高八米、婴儿三岁、婴儿从桥上坠落后会溺水而亡,但客观事实却是桥高五米、婴儿两岁、婴儿的死因是撞到桥墩。就这些主客观的出入而言,修正的风险理论认为,桥高八米和桥高五米可以置换为“桥很高”,婴儿三岁和婴儿两岁可以替代为“婴儿”,溺水与撞到桥墩可以提炼为“从桥上坠落”。
如此一来,新的事实描述就是,“行为人使婴儿从很高的桥上坠落”,这个新的事实描述完全可以构建出一个故意杀人的风险,支撑起故意杀人罪的不法大厦,职是之故,“坠桥案”不阻却行为人故意既遂的刑事责任。

嘉宾点评环节,诸位老师在向蔡圣伟教授表达谢意的同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钢老师认为:
第一,既然故意既遂的审查在通说中也同样存在,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将之作为独立的审查阶层分离出来?
第二,虽然蔡圣伟教授一直在批评通说中有关故意阻却的观点,但通说的真实逻辑却是,故意阻却仅限于行为人未认识到的事实,对于那些行为人已经认识到的事实,故意依然存在。
第三,对应审查中的判断标准与实定法密切相关,各国文字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只有因地制宜,才能较好地适用相关理论。

柏浪涛老师的疑问是:
第一,通说阻却的故意与蔡圣伟教授批评的阻却故意是否为同一个故意?比如甲想用毒果毒死乙,但乙却在吃毒果时噎死,这时通说阻却的其实是甲对乙噎死的故意,而不是想让乙毒死的故意,蔡圣伟教授或许没有分清这两个故意的不同。
第二,故意的认识内容是否包含危险的实现?柏浪涛老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详言之,故意必须由两部分组成,一为认识到当下创设的危险,二为想象出危险将来的实现。如若不然,只要着手一开始,故意就会终局性地成立,行为人将直接成立未遂犯,而再无成立中止犯的空间,因为此时行为人已再无放弃犯意的可能。
唯有将危险实现的想象纳入故意的范畴,才能妥当解决这个问题,亦即在着手后,结果发生前,行为人的故意会持续存在,倘若行为人最后良心发现,决定拯救被害人,那么就可以承认他放弃了先前的犯意,成立犯罪中止。

陈兴良老师提出,诸如打击错误、结果提前实现、结果延后发生、狭义因果关系错误等现象,究竟是不是错误论的问题?换言问之,这些问题到底在客观层面解决,还是在主观层面处理?
比如在打击错误中,行为人其实不存在任何事实误认,行为之所以产生偏差,完全是客观原因所致。甲想开枪杀乙,客观上也向乙开枪,结果乙身手矫健,躲闪及时,子弹与之擦肩而过,却击中远处的丙,在这个案例中,甲不存在任何事实误认,丙的伤亡也并非由甲的认识错误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将打击错误归入错误论的范畴就存在疑问。

梁根林老师的问题是,究竟何为主观构成要件该当性?倘若主观构成要件仅指行为人对客观构成要件诸要素的认识与意欲,那么诚如蔡圣伟教授所言,在主客观构成要件满足之后,确实还缺少一个二者是否对应的审查环节。
但是,如果按照蔡圣伟教授的观点,主观构成要件的认定,是指用与涵射客观事实相同的要素去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想象,那么则可以说,对应的审查其实在这个步骤中就已经完成了,此时再另立一个对应审查阶层,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换言之,当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满足同一套标准时,这套标准的符合本身就意味着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的充分对应。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总干事、管理合伙人王兆峰律师在发言中表示,德恒律师事务所一向注重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与北大有着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后也将长期赞助和支持北大刑法的这样一个理论性的讲座活动。
接下来,王律师提出了一个真实案件,希望在座嘉宾能够用今晚活动所讨论的理论加以检验。该案的具体案情是,甲欲敲诈勒索公司乙,遂向乙的负责人丙放出狠话,称如不给钱就将向公司施以恶害,经过一番周折,甲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可观的金钱。
但是,东窗事发后司法机关却发现,甲得到的钱根本就不归公司乙所有,而是从负责人丙的私人财产中支取。之所以如此,盖因丙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律师的问题是,这个案子是否可以归入事实错误的范畴,理由何在?

韩友谊律师认为,蔡圣伟教授的论证似乎存在逻辑偏误,换言之,客观构成要件结果一旦出现,必然意味着该结果能够归责于行为人,这个结果的发生亦同时确认了既遂的成立。蔡圣伟教授没有说清的是,他所言的结果究竟是未遂结果还是既遂结果,由于二者具有互斥关系,如果是未遂结果,那么就会排除故意既遂的成立;如果是既遂结果,那么就无需再另立一个故意既遂的审查阶层。

最后,车浩老师简短总结了讲座内容和嘉宾们的发言,再次向德恒律师事务所和王兆峰律师表示感谢,并就本次沙龙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车老师认为,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是检验(主客观)事实与(刑法)规范的对应,解决的问题是着手的认定。具体来说,就是分别检验客观事实是否满足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以及主观想象是否满足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例如,在一个杀人案件中,既要检验客观上的行为和结果是否符合杀人罪的客观要素,也要检验行为人主观上的想象是否符合杀人罪的故意。这种检验,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照。在上述对应满足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构成要件的着手。
其二,是检验客观事实与主观事实的对应,解决的问题是既未遂的认定。客观上出现的行为、结果及因果流程,与行为人主观上的想象是否对应。如果出现了两者不对应(诸如客观的因果流程与主观计划的因果流程出现偏离)的情形,就可能影响到既遂的认定。
判断因果流程是否重大偏离的方法,是将客观事实与主观想象的共同部分提取出来,找出二者的最大公约数,再与构成要件的规范标准进行比照,由此得出是否属于重大偏离的结论,进而判断故意既遂是否成立。
由此可见,通常说的错误论,实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想象与实定法规范不一致,比如误将人当作动物杀死,这是与杀人罪要求的“杀人故意”不一致。另一种是主观想象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例如因果流程的偏离,蔡圣伟教授讨论的主题即是这一种。

在回应环节,蔡圣伟教授就各位老师的问题分别予以回应。
针对王钢老师与梁根林老师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将对应审查另立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案件的判断更为清晰,能够倒逼司法者正面回答,为什么在主客观有出入的情况下,依然不妨碍故意既遂的成立。
就柏浪涛老师的问题而言:
第一,甲想毒杀乙,乙却噎死的案例其实不是一个主客观对应审查的问题,而是一种阻却客观归责的情况。详言之,甲制造的毒死乙的风险没有现实化,其间缺少风险关联,直接否认故意杀人罪的客观归责即可。
第二,故意只看着手时,着手后犯意的放弃不影响着手时故意的成立。中止减免的理由是立法者认为,这种情况应当给予犯罪者一定的优待,而不是否定着手时的故意。
陈兴良老师的问题关涉到错误论的范围,有些错误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客观面解决,有些则必须从主观面阐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王兆峰律师的案例,其实也是一种阻却客观构成要件的情况,这是因为,行为人制造的公司财物损失的风险并没有现实化,向公司通告恶害的行为与财物的取得之间欠缺风险关联,敲诈勒索罪的客观归责无法成立。
蔡圣伟教授与车浩老师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与规范的对应部分不仅要确认未遂的成立,而且还要讨论既遂的条件是否满足,换言之,客观构成要件部分要看所有要素是否齐备,而不是只看行为人有没有着手。至于既遂的认定,则与以往的理解有所不同,其不再是客观构成要件的该当,而是不法审查的最后结果,这个理由亦可以充分回答韩友谊律师的问题。
最后,在提问互动环节,蔡圣伟教授为听众答疑解惑,详尽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整个活动在热烈讨论的气氛中持续了将近三个半小时。
最后,车浩老师再次向远道而来的蔡圣伟教授以及各位嘉宾表达谢意,宣布讲座正式结束。
综述:北京大学法学院2017级刑法学博士生 邓卓行
摄影:北京大学法学院2017级刑法学硕士生 陈建苏

1969年5月16日出生于台北,辅仁大学法律系、法研所硕士班毕业,德国弗赖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法学博士,师从沃尔夫冈·弗里施(Wolfgang Frisch)教授。
现为台北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著有《论构成要件选择要素于刑事法上的问题》(Zur Problematik der Tatbestandsalternativen im Strafrecht,2006)、《刑法问题研究》(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