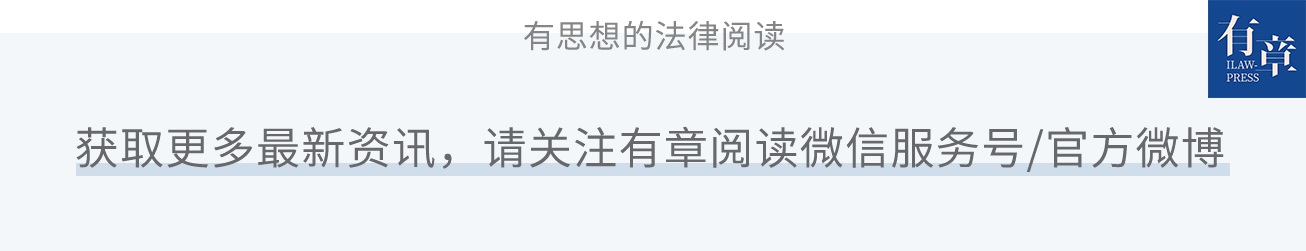始于对刑部驳案的关注,笔者也曾留意到某些对刑部办案的抨击——包世臣向刑部尚书金光悌据理力争,坚持认为拒奸伤翁的儿媳应判无罪,争而不得,愤愤不平将此事写进《齐民四术》中——他还不忘以后续案件验证自己的判断正确:通过邢吴氏拒奸伤翁免罪的案例,刑部确立了嗣后此类案件的处理办法。

但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留给拒奸儿媳的便是坦途。道光年间有人作《驳拒奸议》,直指将拒奸者无罪释放而追究强奸者罪责的立法,未得其平。不平之处在于儿媳所采取的抗拒手段不够深思熟虑,导致其反抗的后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反抗之举也就不乏可责之处:
翁诚兽行,未成奸,义不当绝也。
婉转以求,继之以泣,不得,请死于翁前可也。
请死而得不死,是幸也。请死而竟死,于妇道无亏焉。
处人伦之变,不先自尽其道,激成强暴之势,不得谓之无罪矣。

孙原湘其人,听断经验貌似阙如,其立论有别于包世臣,非为原妇女之情,而是从如何善处“人伦之变”的经与权角度大发议论,其结论是,儿媳应当科以死罪,以刑设教,向吃瓜群众展示:“亲不可殴,虽拒奸必死”。再加上翁奸妇虽未成必死,强奸者与拒奸者都判死刑,这才符合其“平,然后可以为法”的设计。
孙原湘着重阐释的是对作为晚辈、弱者的儿媳的应“于妇道无亏”、不可贸然伤人而“激成强暴之势”的高标准严要求:作为猝遭公公暴力强迫的儿媳,必须一退再退,既要游刃有余选用劝说、求死等非暴力不合作,又要达到拒奸效果。至于翁之罪,因有立法在先,孙原湘并不否认此为“兽行”,但强调儿媳伤翁也是“人断不为”的狠毒,伤翁即是逆伦,即便是出于拒奸,也不值得宽宥。
历史的最大意义、关键作用,就在于反复提醒——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那么天经地义的必然。
——杨照:推理之门由此进
婚姻合二姓之好,异姓夫妻以义合,便有“义绝”,而何时“义绝”?或许是孙原湘与包世臣的根本分歧。
包世臣的观点清晰而坚决,他认为翁起意强奸时,便不配为尊长,事发仓促,儿媳一定程度的反抗,令其公公不敢也不能够继续强迫,也并未造成人死不能复生的严重后果,即便法律上来不及收回尊长的特权和尊崇,情理上也不难接受其拒奸的特殊性质:为了抗拒强奸而伤及强奸者,与因不孝而忤逆公公,固然是同一“伤”,法律性质迥然不同。
孙原湘则坚称:翁诚兽行,未成奸,义不当绝也。这是将义绝的条件提高,对儿媳应如何反抗,设定了完美的标准——即前述“非暴力不合作”的种种尝试。这意味着,翁一刻未得逞,便一刻为尊长。卑幼无助如儿媳,在孙原湘所设计的完美道德世界中,举步维艰,动辄得咎。

未免又想起文学经典:秦可卿自杀前,缠绵病榻,以她对委屈讳莫如深的性格,口口声声说被公婆视若己出,只是自己没福,却在探病的凤姐面前,突然也幽幽来了一句: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可不是么!《红楼梦》也是清人所作——如果贾府的世界里也还讲着孙原湘的规则!
卑幼如此隐忍乖顺,尊长还有何忌惮?色欲炽心,哪有什么王法,还讲什么人伦。儿媳口头拒奸,不为外人所知;公公没苦头吃,有色心又有色胆——同居共财嘛,不妨再找机会。公公一试再试,按孙原湘的“正确对策”,等待儿媳的就两条路:同流合污;死而后已!
先说第二条路。即看似可“留得清白在人间”的以死抗争:《冷庐杂识》载,乾隆年间一起公公欲强奸儿媳,儿媳抓伤公公面部才得免被奸污的案件。儿媳逃过这次,却害怕再次被逼奸,走投无路,因而自尽。这故事扎心的地方在于,儿媳为了让公公彻底断念,为了保全名节而自杀身死,有官员却以她生前毕竟伤翁为由,不肯给她旌表。这在《折狱龟鉴补》的“犯奸”卷中转载,题为“翁逼妇缢”。恰好,前面一则,说的是被逼勉从而又不甘的儿媳,一手导演的家庭悲剧,引自“附会荒唐者多,固不足信,然亦有可益人智者”的《龙图公案》,看题目便心惊胆战——“奸媳淫女”。

选第一条路,即从了公公,当时可以不死,事发就是个死,而且死得千夫所指、名声扫地——道德责备、刑罚加身,打上不守妇道的烙印。此案更有节外生枝,结局令人唏嘘:儿媳是晏东氏,嫁给了晏从义,公公晏某有色心,又方便,“挑之不从,积久难却,乃勉从之”,于是晏从义一出差,晏某夜里“必入媳房”。儿媳恨得要死,没法跟丈夫说,跟娘家人也难以启齿。枝节来了:东氏的小姑子、晏从义的妹妹、晏某的女儿叫金娘,晏从义再出门的时候,金娘被嫂嫂叫来同宿……后来,金娘自杀了。问官定东某之罪:“皆由于汝情可恶”,“乃坐东某于大辟”。这儿媳当然也是死了。
其实,孙原湘没说错——当时的社会,儿媳有层层枷锁无法挣脱。《明刑管见录》是站在拒奸儿媳的一边,设想其悲惨与无助:
试思当其翁调奸之时已无人伦形同禽兽, 若其子妇从之既失名节又不能全生,
及拒伤其翁又干伦纪,
两不相顾之际正忿不欲生之时,
妇人心思既不能保其生自可全其名,此中情节惨也。
如何应对?靠办案者小心调查,“曲予生全”。结合条例嘉庆道光两朝的定例来看,拒奸伤翁勿论,看似贯彻的是包世臣对儿媳的同情;但结合杀翁绞候之例,好像还是孙原湘看得精准,免罪无非“法外施仁”,例虽有局部松动,对“逆伦”的防范仍然坚固——哪怕在强奸者首先不顾伦常、翁媳理当恩断义绝的“拒奸”情境中,儿媳的生路只有一线,一不小心就是万丈深渊。
本文完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