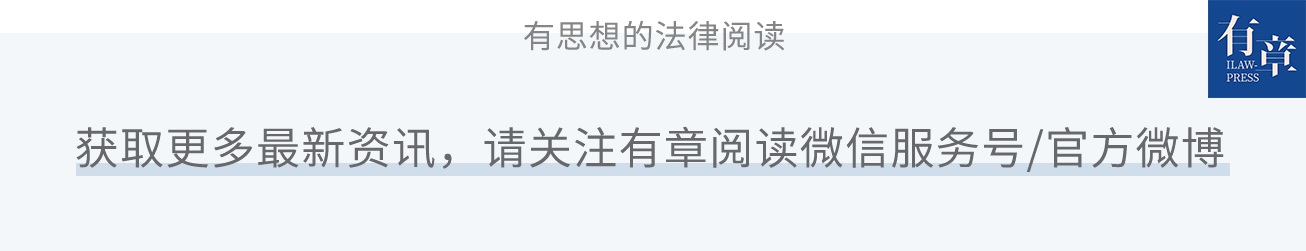今日
荐语
+
曾经有一本书,在被当今政要推荐阅读之前,这本书及其作者,只是极少数象牙塔人士偶尔谈论的话题;在被推荐之后,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他及其作者,以至于倘若不提一提,似乎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学者,似乎就是不关心当下中国命运的读者。这本书就是——畅销多年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被人们热议的写作者托克维尔。
文 | 钟书锋 节选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托克维尔家族姓氏原为“克雷莱尔”。1661年,这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在塞纳河畔的诺曼底取得托克维尔封地后,把姓氏改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全称,一般写成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其实完整的全名是“亚历克西·夏尔·亨利·莫里斯·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1794年,托克维尔曾外祖父、贵族马尔泽尔布由于担任国王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遭大革命政府处死;其正在度蜜月的父母受牵连,也遭大革命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因发生热月政变才得以获释。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亲历法国大革命五大时期(法兰西第*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48年二月革命后曾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后对政治日益失望,退出政界,潜心写书。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历经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等五个“朝代”。托克维尔曾担任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后长期担任众议员,还一度短暂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并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在巴黎聚集对抗政变,遭政变当局逮捕,但在被关押两天后,托克维尔即获释。此后,他对政治日益失望,与英裔妻子隐居乡间城堡,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全书第一卷,第二卷尚未完稿就因病去世。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托克维尔就出版了给他带来盛誉的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在书中,他似乎有一种料事如神的本领,例如,成功预测美国将发生南北战争、美国必将吞并当时尚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美俄两国必将统治全球。在法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托克维尔同样具有预见性,例如,1848年1月27日,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就准确预见法国二月革命即将发生。因此,后世有人把托克维尔尊称为未来学奠基人。
倘若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尤其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不难看出,有着显赫家世和复杂经历的托克维尔,虽然提出了诸多独特见解,但却是一个矛盾而分裂的历史人物,例如:阐述自由时无处不体现卢梭的普世自由和人权理论,却又似乎想竭力否认自己身上的卢梭印记而独尊孟德斯鸠;明明熟读伯克、梯也尔等人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并从中受益良多,却又企图否认那些著作的影响,而且还时不时以尖酸刻薄的笔触讽刺挖苦他们及其著作;自身家族是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却又在多数时候能够冷静分析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辩护者,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者;从宏微观揭示法国贵族的堕落状况,却又认为唯有法国贵族保留了法兰西的自由种子;认同法国包括宗教革命在内的社会革命必然性以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存在无法割断的联动关系,却又天真地梦想政治革命可以与社会革命截然分开;试图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但是,一旦触及实际利益,却又把史学家的客观公正抛到九霄云外;极其崇尚民族自由,以辛辣之笔鞭挞外国在法国大革命后对法国内政的干涉,却又在现实中热烈欢呼英国对中国舟山的侵略行动……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文原著,于1856年出版,是一部研究与反思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其研究视角比较独特。作者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目前出版的这本书,非写法国大革命史。该历史,早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再写。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我们应注意,与主流史学阶段划分不同,他把从1789年起至1849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上台止的六十年,视为一个整体,统称为法国大革命历史时期。
作者运用史学的档案资料研究分析方法、社会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法等等,主要探讨如下内容:1、貌似繁荣昌盛的法国封建王朝,如何堕落衰败,如何不得人心。2、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国大革命,何以背离革命初衷,何以造成社会动荡。3、旨在摧毁一切旧制度的新政权,为何不久又重现旧政权的不少法律制度、治国精神、习惯做法乃至思维模式。总而言之,托克维尔认为:势不可挡的法国大革命,伟大而不美好。
寻章摘句表示自己曾经阅读某书并藉以表达读后感想,似乎是世界通例。作为译者的读者,权且也服从这一习惯,说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历史深思。

从网上网下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最危险之时,往往就是着手改革之际。”有不少人据此引申出一个结论: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对于如此结论,相信九泉之下的托克维尔倘若有知,都会感到无比惊讶。
首先,应当注意,这句语出第三编第四章“旧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何以加速大革命降临”的完整原文,是“就坏政府而言,最危险之时,往往就是着手改革之际”。就是说,托克维尔是针对坏政府而不是好政府作出的判断,好政府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次,要联系上下文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18世纪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王朝,貌似非常繁荣,其实不然,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从史实上考察,就繁荣的主要指标之一财政状况而言,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旧王朝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财政总监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仍然无法解决财政危机,从而被迫召开已停开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托克维尔在前言中就指出:在法国旧王朝这种危害最大的专制社会中,“无所谓安居乐业,人人焦虑不已,渴望挤为人上人,唯恐沦为人下人;金钱,成为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具有独特的流动性,不断转手,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或者降低家庭的社会地位。”托克维尔在正文中进一步揭示,路易十六在位期间存在非常严重的阶层分裂、吏治腐败、司法不独立等重重弊端;在第二编第十二章,专门阐述贵族、有权人、有钱人纷纷抛弃农村迁往城市,造成农村无人过问,底层民众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其境况有时甚至比13世纪时期还更糟糕。
再次,托克维尔在第二编第六章“旧王朝行政管理模式”中,就已明确指出:法国旧王朝政府,“罕见实施最需要实施的改革,或者很快就放弃此种改革。”历史也告诉我们:在1789年前,对于强烈要求实行改革的人民呼声,法国封建王朝政府一直采取漠视、反对甚至镇压的态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积怨已经很深。因此,本质上,法国封建王朝是一个拒绝改革的政府,而且其不少所谓改革,是被逼到墙角时才实施的敷衍改革。
……
有位记者采访我时问,《旧制度与大革命》哪句话最令我印象深刻?答曰:“追求过大自由,就会陷入过大奴役!”这句话,语出本书第三编第一章“文人何以在18世纪中期成为政治权威及其影响”。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派系林立的革命,最终走向革命暴政,走向革命专制,结果导致滥杀无数无辜,非常血腥。用惨遭雅各宾派以莫须有罪名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的临终名言来说,就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自由是有边界的,改革是有边界的,革命也是有边界的,不能不受任何约束,更不能搞一股脑儿的全盘否定,过于激进,过于极端,反而会事与愿违,最终会陷入奴役与被奴役的境地。
“历史大事,近看不如远观”这句话,语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初人们褒贬不一”。它颇有苏轼《题西林壁》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韵味。看历史,往往是越延后往回看,看得就越清楚。比如,评价给我们带来巨大浩劫的那场**大革命,在1970年代,有比在1980年代公允吗?有比在21世纪的现在清醒吗?肯定没有。所以说,尽管在托克维尔之前,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丁等学者撰写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或许这些著作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或者独到的见解,但是,不妨也读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上述两方面,可以说是促使我重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两个原因。当然,重译本书,还有其他考虑。
2012年5月、7月,我先后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选译本)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这两本书都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早在2010年着手翻译这两本书时,我就在想,法国人究竟是如何评价在这两本书指导下发生的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权的?要是翻译完这两本书后,有机会翻译出版反思与研究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会是我翻译过程中的三部曲,就会是比较完美的围绕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的翻译历程。因此,在那时,我就在做有关准备工作,并预计待拙译《论法的精神》与《社会契约论》出版后,一定会有书商或者出版社找上门来,邀请我翻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到2012年8月左右,等来了中国长安出版社项目经理兼北京究竟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金岭先生,他非常恳切地找我翻译出版本书。再到后来,将拙译与商务印书馆译本的部分对照版发到网上后,主动找我或者争取我到其出版社出版拙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社将近十家。

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冯棠译、桂裕芳与张芝联校的首个中译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此时距其第一个法语原版问世整整过去了135年。2012年,该社虽然再版,但并无任何改动。
首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译本的译者,那位已经仙逝的老前辈从无路的茫茫森林地带,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供我行走,而我只不过把这条路拓宽一些而已,只不过把其中的弯弯曲曲拉直一些而已。当然,商务版也给我留下了诸多改进空间:
第一,它是节译本。
商务版译本,是节译本,有五万左右的汉字未翻译。拙译《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但是目前唯一的全译本,而且增加了一百多条交待有关历史、文化、人物、政治、社会、法学等等多方面背景资料的译注,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原著。
第二,它的有些术语译文值得商榷。
例如,它把法文书名“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译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值得商榷。问题出在“Régime”的理解翻译上,该词有“制度”之意,也有“政权”之意。在这里,取“政权”之意似乎更为合理,尤其在正文中,基本上都应取“政权”之意。考虑到大革命前的政权是封建王朝政权,因此,更确切的书名或许应是《旧王朝与大革命》。不过,考虑到经王岐山这么一推荐,也考虑到商务版的巨大影响造成的既定事实,其书名似乎已在大众心目中固定,拙译书名就不作更改,仍然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正文中会采用更为合理的中译文,如译为“王朝”、“政权”等等。
又如,商务版第二编第一章最后一段译文:“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权且不说译文是否简洁通顺,其中的“民事制度”就疑为“社会制度”之误,而且商务版中的“民事制度”都疑为“社会制度”之误。
再如,商务版翻译的原著注释六中的“民政部门”系“政府部门”之误、“风车”系“磨坊”之误。
第三,它的有些人名或者专有名词译文前后不统一。
例如,法国旧王朝行省“Guienne”,商务版有的地方译为“吉耶纳”,有的地方译为“吉耶内”,有的地方译为“基耶内”,让人误以为是不同地名。又如,法国旧王朝的财政总监“Necker”,商务版有的地方译为“内克尔”,有的地方译为“内克”,同一个人不同译文,恐怕不妥。再如,法文“corvées”,商务版一会儿译为“劳役”,一会儿译为“徭役”,很不统一。
第四,它的有些译文令人费解。
例如,商务版第二编第一章第一段“……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其中的“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令人费解。其实,若换成如下拙译,就不难明白其意思:“……在各行省,都有一个代理人,统管一切大小事务;未经允许,其他任何下属,都无权擅自行动;有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案件并袒护政府官员……”
第五,它的有些译文疑欠提炼。
例如,前述的拙译译文“历史大事,近看不如远观”,对应的商务版译文是“近距离不如远距离更能准确地判断历史事件”。又如,本书前言第一段,商务版译文是:“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拙译是:“目前出版的这本书,非写法国大革命史。该历史,早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再写。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一般而言,在汉语中,“发表”与“文章”等搭配,“出版”与“书”等搭配。再如,商务版章节译文,也可以考虑进一步提炼,以更符合汉语行文习惯。
当然,译自法国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2年法文版的拙译,肯定也存在诸多错译、漏译、硬译等问题,恳请诸位大家不吝指正,诚挚感谢!

钟书峰 | 生于1969年5月,江西省龙南县人,法学博士,已翻译作品二百余万字,代表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泰戈尔《萨达那:生命的证悟》等经典作品以及美国《不动产》《美国财产法精解》等专业书籍,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唯一精装收藏全译版
博观译从经典收录
- 唯一全译本 -
★ 貌似繁荣昌盛的法国封建王朝,
如何堕落衰败,如何不得人心?
★ 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法国大革命,
何以背离革命初衷,何以造成社会动荡?
★ 摧毁一切旧制度的新政权,
为何不久又重现旧政权的不少法律制度、
治国精神、习惯做法乃至思维模式?

《天下·博观 旧制度与大革命》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不仅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引发后来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思考与探索的现象与问题。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清楚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拙译是:“目前出版的这本书,非写法国大革命史。该历史,早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再写。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