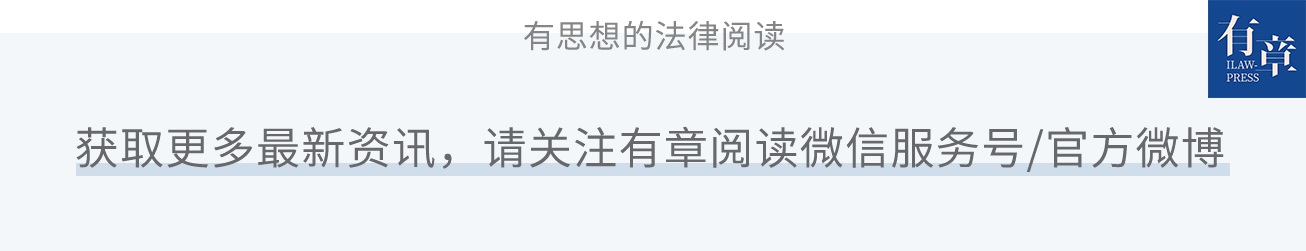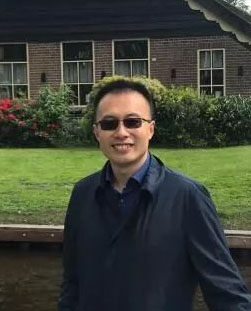
前段时间排队体检,队伍前方有人插队,引起一点骚动。因离我较远,我表达了一下不满,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认为插队不要紧,我为她的“胸襟”表示钦佩。随着队伍的前行,快要排到我们时,前面的这位女士接了一个电话,有位“早有预谋”的朋友想插进队伍来,估计怕我说“闲话”或者还没到,请我站在了她的前面……
这个“插队事件”实际上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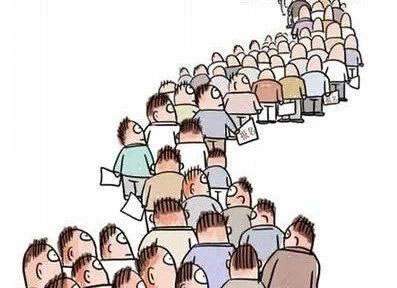
按照规范化排队是绝大多数人的内心需求,也是法治中国实现的根本动力。但是我们看到,有机会插队并获取额外好处的人及其亲友不愿排队并为之寻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现
实生活中插队的机会有可能来源于权力、有可能来源于暴力、也有可能仅仅来源于“机会”。通过反腐败力度加大,权力滥用的成本不断提升;“扫黑除恶”有助于解决暴力产生的机会;剩下的广泛的“机会主义”怎么办?
杜绝插队,构建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法治秩序,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应该树立一个理念,即法治社会的治理模式不是“管制——监督”模式,而是“自律——监督”模式。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依靠“管制——监督”管理社会,不断地增加管制监督者的数量,既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成本降低了社会活力,也总有人监督不着。只有大部分人都自律了,辅之以监督就容易得多了。
因此我觉得,当下法治中国建构的视野要转向如何形成“自律——监督”的模式。
我们发现,支持插队者的说辞有:“人要宽容无争”;“插队可以为有紧要事务的人争取到更多时间,提升效率”;“插队可以现实传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并把插队问题解决不了归结为:“历史原因”“宗教原因”“插队者素质不高”“排队者普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等。
除了这些言论混淆视听外,我们还注意到,插队常态化及获得插队机会的人很乐意享受这种“与众不同”,而当我们普通人遇到插队时看者众、纠者寡,这些都使按照秩序排队显得“困难重重”,甚至导致一些人悲观失望。
但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会排队的,插队也不是哪个民族固有不可更变的,排队形成秩序不是不能实现。
首先,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对秩序和平等等价值的需求已经在人们心中埋下了文明的种子。
其次,有能量插队的人并非都保守顽固,故步自封,其中不乏有社会责任感或有危机意识(怕干起来)的,逐渐转向支持排队或以身作则,可以显见,常态化插队的人数在不断减少。
再次,有些机会主义者在这次排队中可能有个机会插了队,但在下次排队中就可能没有,甚至被别人插了队,因此不是插队的坚定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插队有好处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所以排队,按秩序或者是按法治办事情有群众基础。把插队这个“锅”甩给排队者的漠视说对了一半,负责任的制度设计者要考虑如何激发排队者的公共意识而非听之任之。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是“自律——监督”模式的必要条件。
还需要做到:
一、自律的前提是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才能知晓自己权利的界限,形成有权利且权利在合理的规则时止的普遍意识。
二、营造排队不是“有意为之的稀缺”,而是“随机性稀缺”的社会环境,即便如此,国家也要不断地设计更为明确的预约等可预期性制度,尽可能化解“随机性稀缺”造成的资源紧张,法治本身的可预测性可以淡化人们争抢资源的冲动。
三、公共意识的培养和民众参与、社区、社团实践也会促进人们处理排队等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公民法治意识的基础上,立法有必要对此作出明确的利益衡量,不能简单地诉诸“修心”,甚至像古代那样消灭欲望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不能在人们尚未自律时表现得束手无策。
当然这对立法能力和立法自信是个挑战,而立法能力和立法自信仍然是个结构问题,有效的立法者的来源、组成与立法程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司法机关合适的裁决可以对整个社会“排队是王道”形成明确的指引,要确保裁决机关与插队者没有厉害关系有助于形成裁决机关的公信力,形成有问题找司法而不找政府的生活习惯。
再次,滥执行的问题可以通过监督强化予以部分阻止,引入公众对执行行为的阶段性评估或许是解决选择性执行或者不执行成本最低的手段。“撸起袖子加油干”,再有点耐心,给点时间,形成习惯,排队不是难事。
再往前走一步,文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