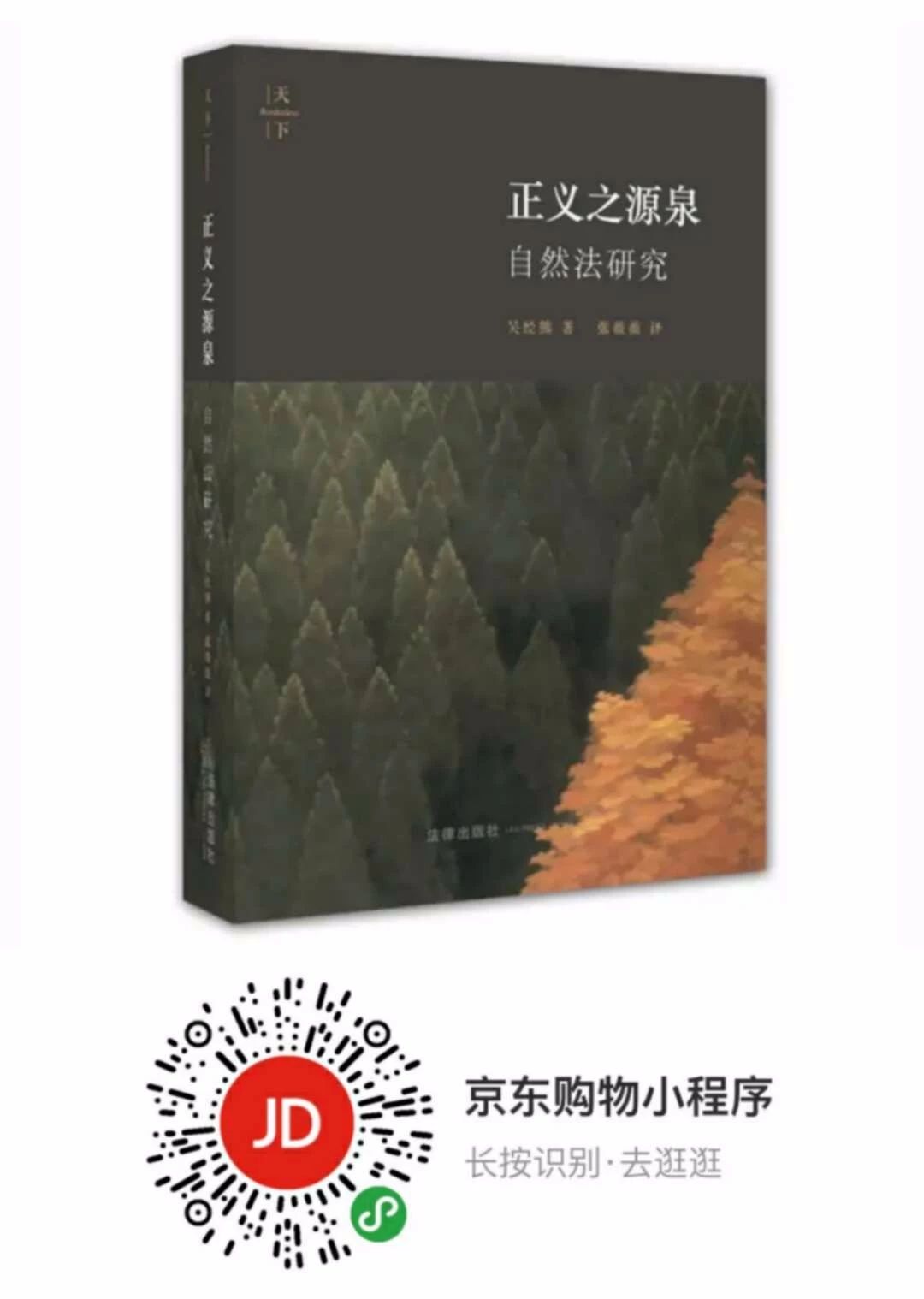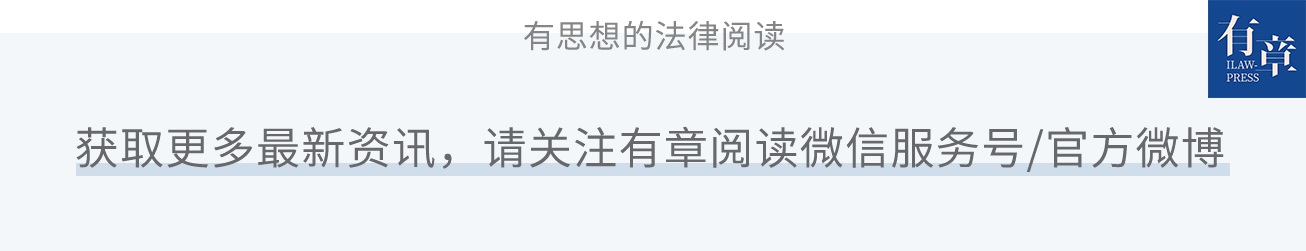在其值得赞叹之文“美国法对于英国法之偏离”中,庞德院长(Dean Pound)以一种合情合理之骄傲(a justifiable pride)评注道:
……美国法之于英国法之最大出离,体现在宪法上。而恰正在此偏向中,美利坚人其实更深沉体现了其之英伦性。吾等已延续并发展了从中世纪至十七世纪英国普通法法院之教义,而英格兰在1688年却以议会绝对主义取代斯图亚特所宣称的皇室绝对主义,远离了普通法律师们所信奉的那些学说。
于古德哈特教授(Professor Goodhart)评注中,吾等可看见大量事实评论道:“英国人的教义所咆哮的那些东西,比它张口去咬的行为还要恶劣。”就以司法审查权(judicial review of Parliamentary Acts)之权限来看,他们已然官方地否定了自然法君临一切(overriding)之权威。

其甚然也。而其不能被想象为:在英格兰,所有当代法官们已完全偏离并异质于以普通法节奏韵调(the commonlaw rhythm)所表达之神法、自然法与国土上的法律。
然而,只要当一项议会立法之合法性、有效性问题未被讨论到,自然法就只能以潜藏于诸如“自然正义与衡平”、“公正与合理的”这般措辞之中或用其他术语来表达之——其假定了补充性的渊源,以其更为谦卑之角色,来填补实证法之漏洞。
法官拜勒斯(Justice Byles)宣称“虽则一部制定法中并无确切语词,要求当事人应被听审,然而普通法院的法官(justice of the common law)将会来填补立法漏洞。”这看起来似乎是:经过司法解释,法庭始终就事实问题(de facto)——如果并非法律问题(de jure)——来控制制定法。
大法官爱斯奎斯(Lord Justice Asquith)说:“只有那些最有说服力之言辞,会让一个法院以一种组合的配备,以使得当事人一方,完全受制于另一方。”
![]()
这就提醒了吾先前的导师——柏林大学的鲁道夫·斯塔姆勒,他主张,没有人应当屈从于另一方之专断意志——一个法律上的命令仅当能以如是之方式——义务人(the obligor)仍会是他的邻居。

如今斯塔姆勒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a neoKantian),他真诚相信自己关于正义之原则之普遍有效;然则他却并不信赖自然法。
或许康德之伦理学,不过乃仅是一种基督教伦理学,其摆脱了可为之提供正当性基础之基督教形而上学体系——它是一个虽然仍显得伟岸之圣殿废墟,带着它暗暗已朽坏了的根基。
吾目前斯塔姆勒之于法与正义之哲学及所有其他法学者那些理念论而非本体论心智(idealistically but not ontologically minded)的学说——就好似吉尔松(Gilson)于康德主义之如上表述。
在家庭法领域中,英国法官们仍然或多或少使普通法仍保持自然法之传统。在一桩涉及父母对于子女之监护权的案子中,博文大法官竟事实上使用了“自然法”这一术语。他说道:“现在,我们的法庭不应忘却且将永不会忘却的首先是家庭生计之权利,其是神圣的。首先,是家庭生活的一些权利,它们是神圣的。”在言及儿童福利之时,他说道,“由法庭来考虑并不必然有益于婴儿,而根据自然法的规则:一位父亲远比法庭法官更懂得怎样对他的孩子好,而这必然有益于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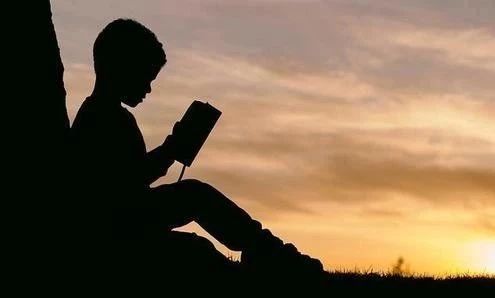
在更新近的一桩类似的判例中,大法官斯雷瑟(Lord Justice Slesser)从圣托马斯之《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援引了两处,
一处是在IIa IIae Q.10,a.12,在那里,圣托马斯言及,“其有违于自然正义,如果一名儿童在开始懂得运用理性以前将其带离父母监护或任何这般有违于其父母意愿之做法,或者因为孩子在其亲关爱之环抱中(这正如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母体子宫的意义)”。
另一处为III Q.68,a.10,在那里圣托马斯说道:如果一个孩子“还不能使用其自由意志,依据自然法他们处于父母关护之下,而只有当他们还未能照顾并主导自己的时候”。
不仅普通法可以做什么,而且是它不能够做什么,让其好比人民的慈爱母亲,一位对于她的孩子们之小错误与弱点故装糊涂之明智妈妈,一位识大体的妈妈。
阿特京法官(Lord Atkin)在拜尔弗诉拜尔弗(Balfour v.Balfour)一案中之观点,正是这样一种人之质素之绝好例子:“普通法并不规范如沐春风之关系中配偶间之种种约定的形式,他们之誓言,并未为盖章或封印。那些于他们而言真正可得之对价(consideration),乃是自然情感与爱情——而这些于冷冰冰之法庭上,却被忽视……在关于承诺(promises)的方面,每一栋房子就是一个领地,国王令状(king’s writ)亦不能发挥作用而获许进入之,官员们也不被许可进入之。”
甚至在家庭法之外,自然法并未全然被禁止。如在1768年,一项由曼斯菲尔德大法官所裁判案件之上诉审中,财税法庭(Court of Exchequer)一致全体判决:“自然法,就是神义之律法(the law of God)……吾等意即应将判决建立于神法基础上,理性原则,道德及普通法基础之上……”
有趣的是并非法庭如何将这些术语概念打包在一起,好比它们都意味着同一种东西。看起来这就像英格兰法官们心智之特点。但他们心灵又不偏不倚、充满善意。他们是实践性的且甚少关注名谓。归根到底正如同其之所思所念:
名为何物?
那莫若玫瑰之谓,
另有祂称,
亦为甜馥。
借同样之精神,法官法维尔(Justice Farwell)宣称,“善与平等(aequum et bonum)这一理念及自然法(ius natural)所流溢出之种种权利构成了英国普通法之一个大部——虽则在英国许多判例之语词当中,‘自然律’(the law of nature)或‘自然法’(natural law)并未经常被提及”。
普通法,如此深地根植于基督教之中而不能完全彻底从自然法传统中剥离:它循有一个对人之高贵理念即人之位格观(human person),将人之生命与自由、理性与社会性设定为最高价值观。它并未厘出明晰之价值尺度。
而若吾等以整体去观之,应能发现:它在人格利益方面较于财产利益方面设置了高得多之价值梯度。
要求一艘船不偏离航道而去救助人命,这是对公共政策之违反;因一艘船以这个目的离开航路并不违反它应当直接赶赴港口目的地之合同之约束。
——贝莱特大法官(Lord Justice Brett)
首席大法官考克班(Chief Justice Cockburn)所想是:如果船之偏航,乃以抢救财物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将不会是优先必要的且要承受所有因为此方面所导致之后果。随之,他做了如下这段有一点理性之哲学的推论:
去解救人之生命于危困中之愿力,乃人性中助益他者之本能之一种……对于所有那些不得不从事航海的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方面人性激发,不应为有关一艘船或船货(a ship or cargo)没有得到必要救助所导致损害后果之吝惜考虑所影响。货物主须被认为在海事法领域之普遍实践中乃以默许之合意——正如其由人性中固有之本能所激发105且建立于所有那些裸露于海上危险之中的人们之共同利益上。
而这恰正是普通法之音。一桩公平合理之审判注定了要为了公益与共同善(common good)服务。一个真正之法理学,须必要时超乎审慎小心或宁可放弃较低遵从较高之审慎。吾等的圣母玛利亚(Our lady)当她从立时流露本心,从未如此优雅且坦诚。首席大法官比斯利(Chief Justice Beasley)就是她的新闻发言官——当他说道,“法律护卫人之生命位格尊严(the lives and persons of men)乃以更大之用心看护,比护卫财产更为甚之。”
在现代型的判例里面,可以引用如下之话来证实之,而一个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则自然法在英格兰被抽去了其形而上或本体论之基础以至于不能再有力量,但其仍含有填补(实在法)漏洞之残余之力。甚至在实证主义时代,只要人还作为人,那么彻底根除自然法,依然无法想像。
事实上于所有现代法律之中,自然法——无论吾等如何称呼它——它仍被视作法源之一。吾只消引述一例予以说明之:
于所有民事案件中在哪儿没有明确法条存在,法官就必定会依据衡平来判案;而当在哪里,实体法保持着缄默,为求判决之公允,法官便会诉诸自然法、理性或业已被广为接受之惯习。